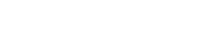观澜城的残垣断壁间,血腥味混著硝烟味瀰漫。
秦军副將王齕一脚踹翻案几,陶碗碎片溅了赵军裨將李信一身。
“废物!都是废物!”
王齕的怒吼震得帐顶落灰:“两千战车!老子带来的两千战车,就这么被秦起那廝烧光了!”
李信抹了把脸上的灰,冷笑一声:“王將军还有脸说?若不是你执意要斩那使者,何至於把秦起逼得动了杀心?现在倒好,神箭手摺了一千三,城墙塌了半截,弟兄们连口水都喝不上。”
“喝不上水怪谁?”
王齕猛地拔剑,剑刃抵在李信咽喉:“当初是谁说观澜城粮草充足,让老子放心推进的?如今粮仓被烧,水源被投了秽物,你倒推得一乾二净!”
帐內的將领们纷纷拔刀,秦军骂赵军弩箭不济,赵军怨秦军战车无用,吵骂声很快变成混战。
一个满脸是血的秦军校尉嘶吼道:“別忘了!咱们可是连下并州七城的虎狼之师!司马进那老东西被咱们追得像条狗,难道还怕一个秦起?”
这话像盆冷水浇下,眾人瞬间停手。
是啊,三个月前,他们踏破并州城门时,司马父子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
可现在……
帐外传来士兵的哭嚎,伤兵们在断墙边呻吟,没人敢去看城墙上那片坍塌的缺口。
“撤吧。”
李信忽然瘫坐在地,声音发颤:“留五千人断后,其余人从西门走。回雍州,再做计较。”
王齕死死盯著帐门,仿佛能透过门板看到秦起的影子。
最终,他將剑狠狠插在地上:“断后?让谁断后?”
“抽籤。”
李信闭上眼:“谁抽中,谁留下。”
……
观锦城军阵前,司马腾第三次请战。
“秦將军!城墙已破,正是攻城之时!”
他的甲冑上还沾著晨露,眼神却燃著烈火:“末將愿带玄甲军为先锋,定能一鼓作气拿下城池!”
秦起摇了摇头,手里把玩著一枚棋子。
那是从窄沟战场捡来的,上面刻著个“卒”字。
“再等等。”
“等什么?”
司马腾急了:“难道要等他们缓过神来?”
“等李蛋。”
秦起將棋子拋向空中,又稳稳接住:“他那边一动,城內必乱。到时候,不用咱们攻,他们自己就会垮。”
身后的將士们却已按捺不住。
姜雄拍著乡军的盾牌,盾面发出沉闷的共鸣:“將军!弟兄们都憋著股劲呢!那十门大炮一响,联军的尿都嚇出来了,此时不攻,更待何时?”
北庭雪也道:“探子回报,联军军营內乱作一团,怕是要逃。”
秦起望向观澜城西门的方向,忽然笑了:“逃?正好。”
待李蛋的信號升起,秦起立马部署,司马腾听闻只围三面,急得红了眼:“放他们走?那我爹的仇……”
“仇要报,但不是现在。”
秦起打断他,声音陡然转沉。
“你以为把他们斩尽杀绝就是痛快?错了。我要让他们活著逃回去,带著一身的伤,满肚子的恐惧,告诉雍州的每一个人,来犯大周者,是什么下场。”
他指向西面的旷野,语气里带著冰碴。
“他们不是连下七城吗?不是觉得咱们好欺负吗?那就让他们一点点退回去,看著咱们收復每一座城,夺回每一寸土地。让他们夜里梦见炮声,白天怕见旌旗,到最后,连提刀的力气都没有。”
姜雄恍然大悟:“將军是要……熬垮他们?”
“正是。”
秦起翻身上马:“玄甲军、赤羽军攻北墙,司马腾攻南墙,武振涛助他。东门归我,西门……留给他们当生路。”
他勒转马头,目光扫过眾將:“记住,不必死战,困住就行。咱们的兵,要留著收復整个并州。”
未时三刻,观澜城西南角忽然升起一股浓烟。
紧接著,吶喊声如潮水般涌来。
“杀秦狗!”
“为家人报仇!”
李蛋举著把菜刀,身后跟著数百百姓,正从西巷杀向联军粮仓。
那些前几日收到短刀的百姓此刻都红著眼,有的举著锄头,有的扛著扁担,將守卫粮仓的少量秦军砍得节节败退。
攻城的號角隨即响起。
玄甲军的黑甲洪流撞向北墙,赤羽军的连弩箭如飞蝗般掠过城头。
南墙下,司马腾的长枪捲起血浪,武振涛的部下扛著云梯紧隨其后。
东门处,秦起的三千乡军列成圆阵,盾手在外,弩手在內,像一块钉死的铁砧。
西门外,王齕带著残部逃窜的模样,比丧家之犬还要狼狈。
士兵们衣衫襤褸,有的光著脚,有的拖著伤腿,甲冑早就不知丟在了哪里。
赵军的神箭手此刻连弓都拉不开,被秦军的败兵推搡著往前跑。
有人摔倒在泥坑里,立刻被后面的人踩成肉泥;
有人抢了同伴的水囊,转身就被一刀捅死。
王齕的披风被扯得只剩半截,髮髻散乱,手里的剑也丟了,只能攥著块石头。
他回头望了眼观澜城,那座曾被他们视为囊中之物的城池,此刻正浓烟滚滚,隱约传来百姓的欢呼。
“大周军队已经攻进城啦!”
“快跑!再快点!”
他嘶吼著,声音里满是恐惧。
李信跟在后面,腿上中了一箭,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他忽然想起出发前,主帅拍著他的肩说:“拿下并州,就封你为郡守”。
如今想来,他妈的神经病啊。
暮色降临时,逃兵们终於衝出西门,却不敢停歇,只顾著往雍州方向狂奔。
他们不知道,秦起正站在东门的断墙上,看著他们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笑。
“传令下去,清点伤亡,安抚百姓。”
他转身走向城內:“派出一支轻骑,遥遥跟著他们。”
“摸清楚他们的动向,他们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必须一路如影隨形,如鬼如魅。”
“如虎驱羊,一刻不停。”
“嚇得他们肝胆俱颤,魂飞魄散为止!”
走到街上,远远地就看到司马腾捧著父亲的尸身,背后跟著无数司马家的亲信。
一路痛哭不止,哀声撼天。
“秦將军。”
北庭雪跟姜雄走上来,眼中也满是动容。
“可惜了,枉死了。”
秦起嘆了一口气。
二人顿时一愣,惊奇地看向秦起。
枉死了?什么意思?
秦军副將王齕一脚踹翻案几,陶碗碎片溅了赵军裨將李信一身。
“废物!都是废物!”
王齕的怒吼震得帐顶落灰:“两千战车!老子带来的两千战车,就这么被秦起那廝烧光了!”
李信抹了把脸上的灰,冷笑一声:“王將军还有脸说?若不是你执意要斩那使者,何至於把秦起逼得动了杀心?现在倒好,神箭手摺了一千三,城墙塌了半截,弟兄们连口水都喝不上。”
“喝不上水怪谁?”
王齕猛地拔剑,剑刃抵在李信咽喉:“当初是谁说观澜城粮草充足,让老子放心推进的?如今粮仓被烧,水源被投了秽物,你倒推得一乾二净!”
帐內的將领们纷纷拔刀,秦军骂赵军弩箭不济,赵军怨秦军战车无用,吵骂声很快变成混战。
一个满脸是血的秦军校尉嘶吼道:“別忘了!咱们可是连下并州七城的虎狼之师!司马进那老东西被咱们追得像条狗,难道还怕一个秦起?”
这话像盆冷水浇下,眾人瞬间停手。
是啊,三个月前,他们踏破并州城门时,司马父子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
可现在……
帐外传来士兵的哭嚎,伤兵们在断墙边呻吟,没人敢去看城墙上那片坍塌的缺口。
“撤吧。”
李信忽然瘫坐在地,声音发颤:“留五千人断后,其余人从西门走。回雍州,再做计较。”
王齕死死盯著帐门,仿佛能透过门板看到秦起的影子。
最终,他將剑狠狠插在地上:“断后?让谁断后?”
“抽籤。”
李信闭上眼:“谁抽中,谁留下。”
……
观锦城军阵前,司马腾第三次请战。
“秦將军!城墙已破,正是攻城之时!”
他的甲冑上还沾著晨露,眼神却燃著烈火:“末將愿带玄甲军为先锋,定能一鼓作气拿下城池!”
秦起摇了摇头,手里把玩著一枚棋子。
那是从窄沟战场捡来的,上面刻著个“卒”字。
“再等等。”
“等什么?”
司马腾急了:“难道要等他们缓过神来?”
“等李蛋。”
秦起將棋子拋向空中,又稳稳接住:“他那边一动,城內必乱。到时候,不用咱们攻,他们自己就会垮。”
身后的將士们却已按捺不住。
姜雄拍著乡军的盾牌,盾面发出沉闷的共鸣:“將军!弟兄们都憋著股劲呢!那十门大炮一响,联军的尿都嚇出来了,此时不攻,更待何时?”
北庭雪也道:“探子回报,联军军营內乱作一团,怕是要逃。”
秦起望向观澜城西门的方向,忽然笑了:“逃?正好。”
待李蛋的信號升起,秦起立马部署,司马腾听闻只围三面,急得红了眼:“放他们走?那我爹的仇……”
“仇要报,但不是现在。”
秦起打断他,声音陡然转沉。
“你以为把他们斩尽杀绝就是痛快?错了。我要让他们活著逃回去,带著一身的伤,满肚子的恐惧,告诉雍州的每一个人,来犯大周者,是什么下场。”
他指向西面的旷野,语气里带著冰碴。
“他们不是连下七城吗?不是觉得咱们好欺负吗?那就让他们一点点退回去,看著咱们收復每一座城,夺回每一寸土地。让他们夜里梦见炮声,白天怕见旌旗,到最后,连提刀的力气都没有。”
姜雄恍然大悟:“將军是要……熬垮他们?”
“正是。”
秦起翻身上马:“玄甲军、赤羽军攻北墙,司马腾攻南墙,武振涛助他。东门归我,西门……留给他们当生路。”
他勒转马头,目光扫过眾將:“记住,不必死战,困住就行。咱们的兵,要留著收復整个并州。”
未时三刻,观澜城西南角忽然升起一股浓烟。
紧接著,吶喊声如潮水般涌来。
“杀秦狗!”
“为家人报仇!”
李蛋举著把菜刀,身后跟著数百百姓,正从西巷杀向联军粮仓。
那些前几日收到短刀的百姓此刻都红著眼,有的举著锄头,有的扛著扁担,將守卫粮仓的少量秦军砍得节节败退。
攻城的號角隨即响起。
玄甲军的黑甲洪流撞向北墙,赤羽军的连弩箭如飞蝗般掠过城头。
南墙下,司马腾的长枪捲起血浪,武振涛的部下扛著云梯紧隨其后。
东门处,秦起的三千乡军列成圆阵,盾手在外,弩手在內,像一块钉死的铁砧。
西门外,王齕带著残部逃窜的模样,比丧家之犬还要狼狈。
士兵们衣衫襤褸,有的光著脚,有的拖著伤腿,甲冑早就不知丟在了哪里。
赵军的神箭手此刻连弓都拉不开,被秦军的败兵推搡著往前跑。
有人摔倒在泥坑里,立刻被后面的人踩成肉泥;
有人抢了同伴的水囊,转身就被一刀捅死。
王齕的披风被扯得只剩半截,髮髻散乱,手里的剑也丟了,只能攥著块石头。
他回头望了眼观澜城,那座曾被他们视为囊中之物的城池,此刻正浓烟滚滚,隱约传来百姓的欢呼。
“大周军队已经攻进城啦!”
“快跑!再快点!”
他嘶吼著,声音里满是恐惧。
李信跟在后面,腿上中了一箭,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他忽然想起出发前,主帅拍著他的肩说:“拿下并州,就封你为郡守”。
如今想来,他妈的神经病啊。
暮色降临时,逃兵们终於衝出西门,却不敢停歇,只顾著往雍州方向狂奔。
他们不知道,秦起正站在东门的断墙上,看著他们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笑。
“传令下去,清点伤亡,安抚百姓。”
他转身走向城內:“派出一支轻骑,遥遥跟著他们。”
“摸清楚他们的动向,他们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必须一路如影隨形,如鬼如魅。”
“如虎驱羊,一刻不停。”
“嚇得他们肝胆俱颤,魂飞魄散为止!”
走到街上,远远地就看到司马腾捧著父亲的尸身,背后跟著无数司马家的亲信。
一路痛哭不止,哀声撼天。
“秦將军。”
北庭雪跟姜雄走上来,眼中也满是动容。
“可惜了,枉死了。”
秦起嘆了一口气。
二人顿时一愣,惊奇地看向秦起。
枉死了?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