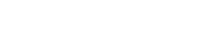反正物资车拉的本就是林湛自己的私人物品,谁也没有多加置喙的资格,又不用他亲自押车,对他而言,车上多两个人跟多两个包裹没区別,他只想让云九倾儘快给他疗伤。
可云九倾却摇了摇头,林湛立刻变了脸色,“你什么意思?
別以为仗著你能治本將军的伤就可以得寸进尺,本將军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林將军的耐心和脾气我已经见识过了,你的信誉,我也见识过了。
所以,为了避免林將军伤愈后不认帐,我们还是立字为据的好。
白纸黑字,我治不好林將军的伤,我认罚,林將军也莫要想著过河拆桥,对谁都公平。”
林湛为长平王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留下马脚。
听云九倾说要立字为据,他下意识地想拒绝。
可仔细想想,只是让几个老弱病残在流放之地动一动,顺便给一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母女搭个便车而已,就算立了字据奈何不得他。
思虑片刻,他便点了头,“来人,笔墨伺候。”
林湛一来,驛丞早早就將驛站最好的房间收拾了出来。
此话一落,驛卒立刻上前,“林將军,我家大人已经为您准备了乾净的上房,將军请。”
林湛连个谢字都不提,他的下属们抬著他就往上房走。
云九倾扭脸冲玄烈招手,“你陪我一起去。”
林湛闻言扭头看他,云九倾理直气壮,“林將军房中皆是一群粗人,我一介妇人,便是乾乾净净的进去,再乾乾净净的出来,旁人一盆污水泼下来,我也是说不清的。
玄烈是王爷的人,让他替我证明清白,林將军应该不会介意吧?”
云九倾说话的时候眼神若有似无的扫过寧二夫人和寧若冰母女,只见那对母女的脸色精彩极了。
她们大概也明白林湛找过其他大夫后再折回来找云九倾,还答应了她那么多要求意味著什么,这会儿虽然不甘心,却不敢再对云九倾说什么了。
林湛现在只想儘快让云九倾为他疗伤,闻言迫不及待的答应了她,“不介意,让他来吧,我们儘快开始治疗。”
有林湛在,驛站里的一切都安排的极为迅速,甚至连字据都很快写好后呈到了云九倾面前,一式两份,双方交换著签了字。
林湛便急切的催促道:“可以开始治疗了吧?”
云九倾大方頷首,“当然,我隨时都可以开始。”
很快,林湛就被放在了一张乾乾净净的床榻上,云九倾跟著上前,“林將军的伤我之前就看过,不用再验。
但我没有傢伙事儿,需要借用一下这位大夫的药箱。”
林湛立刻下令,“把药箱拿过来。”
他甚至没有叫杨大夫,如此一开口,他的下属们直接过去拿杨大夫的药箱。
云九倾冲杨大夫稽首,“不好意思,荒郊野外,只能暂借前辈的药箱一用,我用完立刻还给前辈。”
药箱是大夫吃饭的傢伙事儿,她自己也挺膈应旁人动她的药箱的。
眼下她手里没有傢伙事儿,不得不用杨大夫的药箱,但她对杨大夫还是有著对同行的尊敬的。
后者诧异的愣了一下,隨即鬆开了抓著药箱背带的手,“无妨、无妨……”
杨大夫意识到眼前的少女应该就是林湛口中那位可以让林湛那种伤癒合到仅仅是瘸腿的地步的大夫了。
没想到想像了一路的神医不但是个女人,还如此年轻。
杨大夫下意识的將药箱递给官差后,才不確定道:“林將军的伤老朽看过,筋脉、骨头、皮肉俱有损伤。
那等情况,只怕是宫中最好的御医来了,也顶多是保那条腿不被截肢,让他看上去四肢齐全而已,那条腿想要受力、甚至走路都是不可能的。
林將军却说,姑娘能將他的伤治到仅仅是走路有一点瘸,不知此话可当真?”
“自然是真的。”
云九倾指了指身上的囚服,“我一个流放犯,如何敢拿这种事情与林將军吹牛?
若是没有点儿真本事,治不好林將军,或者治得不如自己说的,我的日子岂不是很惨?”
杨大夫也是看著云九倾身上的囚服才觉得她应该不敢骗林湛的。
见云九倾態度也还算柔和,便主动开口,“老夫穷尽毕生所学都无法达到姑娘所说的疗效,不知姑娘给林將军疗伤的时候,老朽可否旁观一番?”
云九倾闻言脚步微顿,语带戏謔,“林將军带前辈来此,难道不就是为了观看我的治疗过程,我有拒绝的权力?”
哪怕林湛已经答应立字为据了,可云九倾心里清楚的很,只要自己治疗的效果没达到林湛的预期,他还是会想方设法的报復她。
而杨大夫的话就是评判她在治疗过程中有没有尽心尽力,是否动了手脚的標准。
杨大夫虽然在问她,可实际上林湛根本不会给她拒绝杨大夫旁观的权力。
杨大夫明知故问被揭穿也不觉得尷尬,反而一脸坦然的与云九倾对视,“难道姑娘方才与老朽借药箱时觉得老朽有拒绝的权力?”
语毕,二人相视一笑,云九倾低头探上了林湛的脉,不过须臾,她便开口,“用过止疼化瘀的药了?”
“用过了。”
杨大夫頷首,“林將军之前疼的厉害,而且不消肿化瘀,后面的治疗无法进行。
老朽临时做了些应急的措施,不会耽搁姑娘治疗吧?”
云九倾摇摇头,“你做的是对的,但你既然有此常识,为何不对他的伤口进行初步的包扎和固定?
这一上午搬来搬去的,骨头都错位了,现在正骨復位,又得白白遭诸多罪,真是……,帮我找些平直的模板来,还有绷带。”
东西没到,治疗无从进行,她抬头毫不客气的使唤林湛的下属,“拿笔墨来,我要开药方。”
官差得了林湛的首肯才下去拿纸笔,云九倾则边为林湛清理伤口,边问他,“按理说,以你这情况,服用汤药疗效最好。
但咱们现在是在被流放的路上,我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机会按时煎药服药。
实在不行的话將药材製成药碗按时服用也可以,就是疗效会比服用汤药慢一些,不知林將军作何打算?”
嘴上说著话,手里的银针已经扎在了林湛身上。
可云九倾却摇了摇头,林湛立刻变了脸色,“你什么意思?
別以为仗著你能治本將军的伤就可以得寸进尺,本將军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林將军的耐心和脾气我已经见识过了,你的信誉,我也见识过了。
所以,为了避免林將军伤愈后不认帐,我们还是立字为据的好。
白纸黑字,我治不好林將军的伤,我认罚,林將军也莫要想著过河拆桥,对谁都公平。”
林湛为长平王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留下马脚。
听云九倾说要立字为据,他下意识地想拒绝。
可仔细想想,只是让几个老弱病残在流放之地动一动,顺便给一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母女搭个便车而已,就算立了字据奈何不得他。
思虑片刻,他便点了头,“来人,笔墨伺候。”
林湛一来,驛丞早早就將驛站最好的房间收拾了出来。
此话一落,驛卒立刻上前,“林將军,我家大人已经为您准备了乾净的上房,將军请。”
林湛连个谢字都不提,他的下属们抬著他就往上房走。
云九倾扭脸冲玄烈招手,“你陪我一起去。”
林湛闻言扭头看他,云九倾理直气壮,“林將军房中皆是一群粗人,我一介妇人,便是乾乾净净的进去,再乾乾净净的出来,旁人一盆污水泼下来,我也是说不清的。
玄烈是王爷的人,让他替我证明清白,林將军应该不会介意吧?”
云九倾说话的时候眼神若有似无的扫过寧二夫人和寧若冰母女,只见那对母女的脸色精彩极了。
她们大概也明白林湛找过其他大夫后再折回来找云九倾,还答应了她那么多要求意味著什么,这会儿虽然不甘心,却不敢再对云九倾说什么了。
林湛现在只想儘快让云九倾为他疗伤,闻言迫不及待的答应了她,“不介意,让他来吧,我们儘快开始治疗。”
有林湛在,驛站里的一切都安排的极为迅速,甚至连字据都很快写好后呈到了云九倾面前,一式两份,双方交换著签了字。
林湛便急切的催促道:“可以开始治疗了吧?”
云九倾大方頷首,“当然,我隨时都可以开始。”
很快,林湛就被放在了一张乾乾净净的床榻上,云九倾跟著上前,“林將军的伤我之前就看过,不用再验。
但我没有傢伙事儿,需要借用一下这位大夫的药箱。”
林湛立刻下令,“把药箱拿过来。”
他甚至没有叫杨大夫,如此一开口,他的下属们直接过去拿杨大夫的药箱。
云九倾冲杨大夫稽首,“不好意思,荒郊野外,只能暂借前辈的药箱一用,我用完立刻还给前辈。”
药箱是大夫吃饭的傢伙事儿,她自己也挺膈应旁人动她的药箱的。
眼下她手里没有傢伙事儿,不得不用杨大夫的药箱,但她对杨大夫还是有著对同行的尊敬的。
后者诧异的愣了一下,隨即鬆开了抓著药箱背带的手,“无妨、无妨……”
杨大夫意识到眼前的少女应该就是林湛口中那位可以让林湛那种伤癒合到仅仅是瘸腿的地步的大夫了。
没想到想像了一路的神医不但是个女人,还如此年轻。
杨大夫下意识的將药箱递给官差后,才不確定道:“林將军的伤老朽看过,筋脉、骨头、皮肉俱有损伤。
那等情况,只怕是宫中最好的御医来了,也顶多是保那条腿不被截肢,让他看上去四肢齐全而已,那条腿想要受力、甚至走路都是不可能的。
林將军却说,姑娘能將他的伤治到仅仅是走路有一点瘸,不知此话可当真?”
“自然是真的。”
云九倾指了指身上的囚服,“我一个流放犯,如何敢拿这种事情与林將军吹牛?
若是没有点儿真本事,治不好林將军,或者治得不如自己说的,我的日子岂不是很惨?”
杨大夫也是看著云九倾身上的囚服才觉得她应该不敢骗林湛的。
见云九倾態度也还算柔和,便主动开口,“老夫穷尽毕生所学都无法达到姑娘所说的疗效,不知姑娘给林將军疗伤的时候,老朽可否旁观一番?”
云九倾闻言脚步微顿,语带戏謔,“林將军带前辈来此,难道不就是为了观看我的治疗过程,我有拒绝的权力?”
哪怕林湛已经答应立字为据了,可云九倾心里清楚的很,只要自己治疗的效果没达到林湛的预期,他还是会想方设法的报復她。
而杨大夫的话就是评判她在治疗过程中有没有尽心尽力,是否动了手脚的標准。
杨大夫虽然在问她,可实际上林湛根本不会给她拒绝杨大夫旁观的权力。
杨大夫明知故问被揭穿也不觉得尷尬,反而一脸坦然的与云九倾对视,“难道姑娘方才与老朽借药箱时觉得老朽有拒绝的权力?”
语毕,二人相视一笑,云九倾低头探上了林湛的脉,不过须臾,她便开口,“用过止疼化瘀的药了?”
“用过了。”
杨大夫頷首,“林將军之前疼的厉害,而且不消肿化瘀,后面的治疗无法进行。
老朽临时做了些应急的措施,不会耽搁姑娘治疗吧?”
云九倾摇摇头,“你做的是对的,但你既然有此常识,为何不对他的伤口进行初步的包扎和固定?
这一上午搬来搬去的,骨头都错位了,现在正骨復位,又得白白遭诸多罪,真是……,帮我找些平直的模板来,还有绷带。”
东西没到,治疗无从进行,她抬头毫不客气的使唤林湛的下属,“拿笔墨来,我要开药方。”
官差得了林湛的首肯才下去拿纸笔,云九倾则边为林湛清理伤口,边问他,“按理说,以你这情况,服用汤药疗效最好。
但咱们现在是在被流放的路上,我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机会按时煎药服药。
实在不行的话將药材製成药碗按时服用也可以,就是疗效会比服用汤药慢一些,不知林將军作何打算?”
嘴上说著话,手里的银针已经扎在了林湛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