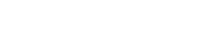那日在驛站附近的布庄买了布料,可寧氏女眷虽然会做衣服,但她们在家里时也就偶尔给自己的丈夫和儿女做一身衣服而已,速度到底快不了。
以至於过去这么多日,云九倾他们还是没能拿到自己的衣服。
寧三夫人也是知道这一点,才敢跟云九倾和谢辞渊开口的。
就在这时,寧大夫人抱著浑身湿透的寧媛过来了,小姑娘浑身湿漉漉的,手里抱著一个大碗。
寧大夫人柔柔笑著,“王妃,我从厨房找了一些红和姜粉沏了一碗红姜水,您赶紧喝了。
王爷的身子本就不好,您可不能再倒下。”
寧媛亦小心翼翼的捧著那碗红姜水往云九倾面前递过去,“王妃嫂嫂,给。”
寧三夫人本来就强撑著的笑脸登时垮了下去。
云九倾对寧媛的喜欢他们都看在眼里,而且她也的確不似寧大夫人那般周全,握著两个拳头就过来了。
寧三夫人自觉求助无望,正要离开,就听云九倾道:“好啊,三舅母过来坐便是,这一大碗红姜水我一个人哪儿喝得完,我们几个一起吧。”
她接过那碗红姜水猛灌了一口便递给了寧媛,转而对谢辞渊等人道:“你们几个大男人就没份儿了,往边上让一让,冷的话到那边去打打拳就热了。”
嘴上这么说著,实际上柴火点起来的火堆不算小,也不差那几个人的位置。
她蹲在谢辞渊身边摸上了谢辞渊的脉搏,“还好,没有著凉。”
顺手拉著寧媛的手把小姑娘抱到了身前,“好不容易退了烧,可別再著凉了。”
小姑娘已经习惯了云九倾的亲近,缩在她怀里缩了缩脖子,嘿嘿笑出来,“王妃嫂嫂身上好香……”
“哪有?”
云九倾狐疑的抬胳膊嗅了嗅,“连著赶路,还没换衣服,不发臭就好了,哪儿还能有什么香味?”
寧大夫人倾身嗅了一下,“还真不是媛媛胡说,王妃身上真的透著一股难言的香味。
三弟妹,你来看看是不是?”
寧三夫人正扶著寧老夫人过来烤火,闻言纳闷,“什么是不是?”
“大家连著赶路,又淋雨又暴晒的,身上都臭了,可王妃身上香香的,她自己还闻不到……”
“是吗?”
寧三夫人其实並不相信寧大夫人的话,还以为寧大夫人是为了討好云九倾,让其继续照拂他们才故意说云九倾的好话。
只是出於凑热闹的心思过去一闻,却被惊到了,“王妃,您不会被流放了还带著薰香吧?”
狐疑的眼神迅速而周密的將云九倾浑身打量了一遍,像是势要將云九倾身上的香味来源找出来。
云九倾简直哭笑不得,“哪有什么香味啊,你们……”
“王妃身上的不是香料的味道,而是久处药房,常年与药材打交道才生出的药香。”
寧老夫人说了这么一句,才將视线落在谢辞渊身上,“素闻明慧郡主医术过人,当年楚京女眷最是喜欢向明慧郡主求医问药,倒是不知王妃竟也承袭了明慧郡主的衣钵。
却不知王妃的医术,能不能治王爷的伤?”
这是被流放的十多天里寧老夫人第一次主动与云九倾搭话。
所有人都淋了雨,寧老夫人自然也没能例外。
她的头髮有些乱了,衣服也脏乎乎的,被寧三夫人搀扶著坐在了廊檐下的长椅上。
她手里拄著前几日云九倾用树枝做的拐杖,身子微微靠在身后的栏杆上,姿態也有些狼狈。
比起那些口口声声说著被流放了也要保持体面的官眷,她看著並不太像是富贵过的人,说出口的话亦彰显著她非同一般的见识。
云九倾不太了解这位老夫人,也没兴趣了解,只当她是关心谢辞渊,顺势道:“老夫人过誉了,我只是略通岐黄之术,算不得继承了母亲的衣钵。
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王爷的伤有很多重因素的叠加,流放途中亦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让王爷的伤不再恶化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想治好,怕是有点难。”
寧老夫人眉眼沉静的望著云九倾,神情一派柔和,说出口的话却令云九倾心梗。
只听她道:“哦,是吗?
我怎么听说那林湛中的是和王爷一样的毒?
同样的条件,能给那林湛治,却不能给王爷治?”
正蹲在火堆旁烤火的玄烈几人像是被针炸了屁股似的瞬间弹了起来。
惊悚的眼神盯著寧老夫人,简直不敢置信他们极力隱瞒的事情就这么被寧老夫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说了出来。
云九倾下意识的去看林湛那边,郑鐸显然也听到了寧老夫人的话,直接衝到了云九倾面前,“我家將军和宴王中的是同一种毒?
为何你从未说过?”
云九倾在心里直骂娘,她防著王靖康和林湛的窥探,防著寧若冰因爱生恨,防著寧若愚脑子进水。
千防万防,万万没想到这位一上来就直接给她来了个滑铲。
心里直接化作了喷火龙,面上却还要应付郑鐸的质问,“我也不知道你家將军和我家王爷中的是同一种毒啊?
我一直以为我家王爷是因为断了经脉才站不起来的。
你既然如此相信承恩公夫人的话,不若你请承恩公夫人去给你家將军看看,说不定等承恩公夫人看过,你家將军明天就健步如飞了呢?”
玄清以冷声附和,“就是,这么相信別人,就別来找我家王妃治病啊!
又要用王妃,又不相信她,跑去相信一个连医书都没怎么碰过的內宅妇人,你脑子没毛病吧?”
郑鐸其实也就是太紧张林湛的伤了,毕竟她不是普通的护卫,而是长平王赐予林湛的暗卫。
以长平王管理暗卫的规矩,林湛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伤成这样,他回去也是要脱层皮的,以至於他一听到寧老夫人的话就立刻衝出来质问云九倾。
被云九倾和玄清相继怒懟,他才反应过来,目前的云九倾不是他能得罪的。
不过郑鐸是官,云九倾是犯,让他认错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跟在林湛身边处理各种棘手的事宜,也不至於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乱了分寸。
稍稍发蒙之后,他疑惑的眼神在云九倾和寧老夫人之间来回巡视数遍,表情真诚极了,“在下想著你们是一起的,听寧老夫人这么说,还以为是王妃告诉她的呀?
原来不是吗,那是我误会了。”
以至於过去这么多日,云九倾他们还是没能拿到自己的衣服。
寧三夫人也是知道这一点,才敢跟云九倾和谢辞渊开口的。
就在这时,寧大夫人抱著浑身湿透的寧媛过来了,小姑娘浑身湿漉漉的,手里抱著一个大碗。
寧大夫人柔柔笑著,“王妃,我从厨房找了一些红和姜粉沏了一碗红姜水,您赶紧喝了。
王爷的身子本就不好,您可不能再倒下。”
寧媛亦小心翼翼的捧著那碗红姜水往云九倾面前递过去,“王妃嫂嫂,给。”
寧三夫人本来就强撑著的笑脸登时垮了下去。
云九倾对寧媛的喜欢他们都看在眼里,而且她也的確不似寧大夫人那般周全,握著两个拳头就过来了。
寧三夫人自觉求助无望,正要离开,就听云九倾道:“好啊,三舅母过来坐便是,这一大碗红姜水我一个人哪儿喝得完,我们几个一起吧。”
她接过那碗红姜水猛灌了一口便递给了寧媛,转而对谢辞渊等人道:“你们几个大男人就没份儿了,往边上让一让,冷的话到那边去打打拳就热了。”
嘴上这么说著,实际上柴火点起来的火堆不算小,也不差那几个人的位置。
她蹲在谢辞渊身边摸上了谢辞渊的脉搏,“还好,没有著凉。”
顺手拉著寧媛的手把小姑娘抱到了身前,“好不容易退了烧,可別再著凉了。”
小姑娘已经习惯了云九倾的亲近,缩在她怀里缩了缩脖子,嘿嘿笑出来,“王妃嫂嫂身上好香……”
“哪有?”
云九倾狐疑的抬胳膊嗅了嗅,“连著赶路,还没换衣服,不发臭就好了,哪儿还能有什么香味?”
寧大夫人倾身嗅了一下,“还真不是媛媛胡说,王妃身上真的透著一股难言的香味。
三弟妹,你来看看是不是?”
寧三夫人正扶著寧老夫人过来烤火,闻言纳闷,“什么是不是?”
“大家连著赶路,又淋雨又暴晒的,身上都臭了,可王妃身上香香的,她自己还闻不到……”
“是吗?”
寧三夫人其实並不相信寧大夫人的话,还以为寧大夫人是为了討好云九倾,让其继续照拂他们才故意说云九倾的好话。
只是出於凑热闹的心思过去一闻,却被惊到了,“王妃,您不会被流放了还带著薰香吧?”
狐疑的眼神迅速而周密的將云九倾浑身打量了一遍,像是势要將云九倾身上的香味来源找出来。
云九倾简直哭笑不得,“哪有什么香味啊,你们……”
“王妃身上的不是香料的味道,而是久处药房,常年与药材打交道才生出的药香。”
寧老夫人说了这么一句,才將视线落在谢辞渊身上,“素闻明慧郡主医术过人,当年楚京女眷最是喜欢向明慧郡主求医问药,倒是不知王妃竟也承袭了明慧郡主的衣钵。
却不知王妃的医术,能不能治王爷的伤?”
这是被流放的十多天里寧老夫人第一次主动与云九倾搭话。
所有人都淋了雨,寧老夫人自然也没能例外。
她的头髮有些乱了,衣服也脏乎乎的,被寧三夫人搀扶著坐在了廊檐下的长椅上。
她手里拄著前几日云九倾用树枝做的拐杖,身子微微靠在身后的栏杆上,姿態也有些狼狈。
比起那些口口声声说著被流放了也要保持体面的官眷,她看著並不太像是富贵过的人,说出口的话亦彰显著她非同一般的见识。
云九倾不太了解这位老夫人,也没兴趣了解,只当她是关心谢辞渊,顺势道:“老夫人过誉了,我只是略通岐黄之术,算不得继承了母亲的衣钵。
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王爷的伤有很多重因素的叠加,流放途中亦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让王爷的伤不再恶化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想治好,怕是有点难。”
寧老夫人眉眼沉静的望著云九倾,神情一派柔和,说出口的话却令云九倾心梗。
只听她道:“哦,是吗?
我怎么听说那林湛中的是和王爷一样的毒?
同样的条件,能给那林湛治,却不能给王爷治?”
正蹲在火堆旁烤火的玄烈几人像是被针炸了屁股似的瞬间弹了起来。
惊悚的眼神盯著寧老夫人,简直不敢置信他们极力隱瞒的事情就这么被寧老夫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说了出来。
云九倾下意识的去看林湛那边,郑鐸显然也听到了寧老夫人的话,直接衝到了云九倾面前,“我家將军和宴王中的是同一种毒?
为何你从未说过?”
云九倾在心里直骂娘,她防著王靖康和林湛的窥探,防著寧若冰因爱生恨,防著寧若愚脑子进水。
千防万防,万万没想到这位一上来就直接给她来了个滑铲。
心里直接化作了喷火龙,面上却还要应付郑鐸的质问,“我也不知道你家將军和我家王爷中的是同一种毒啊?
我一直以为我家王爷是因为断了经脉才站不起来的。
你既然如此相信承恩公夫人的话,不若你请承恩公夫人去给你家將军看看,说不定等承恩公夫人看过,你家將军明天就健步如飞了呢?”
玄清以冷声附和,“就是,这么相信別人,就別来找我家王妃治病啊!
又要用王妃,又不相信她,跑去相信一个连医书都没怎么碰过的內宅妇人,你脑子没毛病吧?”
郑鐸其实也就是太紧张林湛的伤了,毕竟她不是普通的护卫,而是长平王赐予林湛的暗卫。
以长平王管理暗卫的规矩,林湛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伤成这样,他回去也是要脱层皮的,以至於他一听到寧老夫人的话就立刻衝出来质问云九倾。
被云九倾和玄清相继怒懟,他才反应过来,目前的云九倾不是他能得罪的。
不过郑鐸是官,云九倾是犯,让他认错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跟在林湛身边处理各种棘手的事宜,也不至於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乱了分寸。
稍稍发蒙之后,他疑惑的眼神在云九倾和寧老夫人之间来回巡视数遍,表情真诚极了,“在下想著你们是一起的,听寧老夫人这么说,还以为是王妃告诉她的呀?
原来不是吗,那是我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