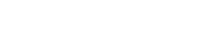魏凡的夸讚让钟铭脸上掠过一丝自得。
他哈哈一笑,举起手中那只粗陶小酒罈回敬:“公子好见识!此酒乃用上等三月杏……”
话音未落,
异变陡生!
“嗖!嗖!嗖——!”
一道悽厉的破空声撕裂雨幕,压过庙外轰隆的雷声,尖锐得令人头皮发麻!
紧接著,
便是数声短促而悽厉的惨嚎,如同被掐断喉咙的野兽,猛地灌入土庙。
眾人骇然望去,
只见原本守在庙门口的数名青衣汉子,如同被重锤击中,身躯剧震,踉蹌几步后,纷纷翻身栽倒在泥泞的门槛边。
冰冷的雨水冲刷著他们身上斜插而入的数支短小精悍、闪著幽蓝寒光的弩箭。
箭尾兀自震颤,血水混合著雨水,迅速在身下洇开。
“什么人?!”
钟铭与锦袍女子同时色变,惊喝出声。
钟铭反应快如闪电,
“沧啷——”一声,腰间长剑已然出鞘,寒光乍现,瞬间横在锦袍女子身前。
他双目如电扫向门外,厉声喝道:“护住小姐!!”
土庙內,其余青衣汉子虽惊不乱,训练有素的素质在此刻显现。
他们低吼一声,迅速收缩阵型,刀剑齐出,鏗鏘作响,顷刻间將钟铭与锦袍女子护在中间。
人人面色紧绷,紧盯著那洞开的、被风雨不断灌入的庙门。
另一边,
那李福全一家三口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血腥变故嚇得魂飞魄散。
妇人抱著孩子发出压抑的尖叫,男人李福全面无人色,连滚带爬地拖著妻儿,哭喊著缩向那尊残破神像之后,恨不得將身体嵌进冰冷的泥墙里。
“嗤拉——!”
又一道惨白的电蛇撕裂墨黑的苍穹,將破庙內外照得一片森然诡亮。
惨白的电光下,泥水横流,尸体伏地,兵刃寒光闪烁,映照著每一张惊惶或决绝的脸。
“嘿嘿嘿……”
一阵怪异、嘶哑,如同夜梟啼哭般的笑声,伴隨著沉重的脚步声,穿透雨幕,清晰地传入庙內。
电光再闪!
两道身影,一高一矮,已然无声无息地矗立在庙门之外,雨水顺著他们紧贴身体的黑色夜行衣流淌,倒是更添几分阴森。
高的那人,瘦长如竹,几乎比常人高出两头,面颊上赫然一块碗口大小、边缘狰狞的墨黑色胎记。
矮的那位,身高不过五六尺,身形佝僂得厉害,
然而其身后,竟斜背著一柄足有一人半高、刀身宽阔、刃口在电光下泛著冷冽青芒的巨型偃月刀。
“桐山双煞?!”
钟铭瞳孔骤然收缩,失声惊呼,握剑的手心瞬间沁出冷汗。
这二人,乃是十几年前镜州城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煞星!
凶名赫赫,犯下累累血案,手段残忍至极。
更可怕的是,这对兄弟皆是踏入后天境界多年的高手,一身横练功夫与诡异刀法配合无间,当年不知多少江湖好手摺在他们手下。
最终是镜州城几大势力联手围剿,付出不小代价才將这双魔头逐出镜州地界。
他们怎会在此刻出现?!
“嘿嘿嘿…”
那佝僂的矮个子怪笑几声,声音如同砂纸摩擦,他扭了扭脖子,发出咔吧脆响,
“想不到十几年过去,镜州城这腌臢地界,还有人记得我们兄弟的名头?”
他浑浊的小眼睛扫过钟铭,带著一丝扭曲的满意,“不错不错,你这小娃娃记性倒好,待会儿爷爷开恩,留你一个囫圇尸首!”
明明看上去年纪与钟铭相仿,却一口一个“小娃娃”、“爷爷”地叫著,其乖戾张狂之態,令人遍体生寒。
“大兄,其他杂鱼都给你消遣,”
那瘦长如竹竿的高个男子狞笑著接口,一双淫邪的眼珠却死死钉在角落锦袍女子那惊惧煞白的俏脸上,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十几年没开荤,都快忘了娘们儿是什么滋味了…这小娘子细皮嫩肉,归我了!”
话语中的污秽之意,让锦袍女子身边的健妇和丫鬟脸色惨白如纸,浑身发抖。
土庙之中,义安鏢局尚有二十余条精悍汉子,更有钟铭这等一流好手压阵。
可在这桐山双煞眼中,竟似视若无物一般。
“混帐!”
钟铭怒髮衝冠,厉声喝骂,心中却涌起惊涛骇浪,
“尔等魔头,十几年前已被各帮各派联手逐出镜州!如今怎敢回来?不怕再遭围剿,死无葬身之地?!”
“若不是那些大人物点了头,我们兄弟二人怎敢回来?真以为镜州城那些个什么江湖帮派就值得我们二人畏惧吗?”
那位身材佝僂的中年男子似是不屑的嗤笑一声,接著又慢悠悠的说道:
“放心,到时候不光你们义安鏢局,整个镜州城都要大变天的。”
“什么?!”
钟铭如遭雷击,心猛地沉入深渊。
他自幼在镜州城长大,半生心血都倾注在义安鏢局。
若桐山双煞所言非虚,那镜州城將迎来一场可怕的风暴,鏢局…危矣!
这消息带来的衝击,甚至比眼前的凶险更让他心如刀绞。
周围的青衣汉子们闻言,亦是面无人色,眼中流露出绝望。
“大变天么…”
火堆旁,魏凡依旧盘坐,仿佛置身事外,只是口中低不可闻地喃喃了一句,眼中若有所思,“看来这镜州城,果然不太平了。”
“大兄,何必跟这些將死之人废话!”
那瘦长高个早已按捺不住,眼中淫邪与杀意交织,“料理了他们,回城还有正事要做!”
话音未落,他佝僂矮小的大兄尚未动作,这瘦长身影却已如鬼魅般动了!
没有预兆,没有蓄力。
只见黑影一闪,那瘦长男子竟已越过数丈距离,无视挡在前方的眾多鏢师,如同瞬移般欺近到钟铭身前。
他右手两指併拢,指甲乌黑尖利,竟如毒蛇吐信,带著刺耳的锐啸,直插钟铭右侧太阳穴!
指尖未至,那阴冷的劲风已刺得钟铭太阳穴肌肤生疼!
太快了!
钟铭脑中一片空白,眼睁睁看著那双指如死亡之矛逼近,全身气力仿佛被瞬间抽空,连格挡的念头都来不及升起!
死亡的阴影瞬间將他笼罩。
“完了!”一个绝望的念头在他心中炸开。
然而,就在那乌黑指尖即將触及皮肤的剎那——
“嗖!”
一声轻微到几乎被雨声淹没的破空声响起。
一根寻常可见、拇指粗细、带著湿漉漉树皮的枯枝,如同被无形的弓弩射出,从庙內某个角落斜斜飞来。
它穿过混乱紧张的人群缝隙,轨跡刁钻无比,速度快逾闪电一般。
噗嗤!
一声轻响,如同石子投入烂泥。
那根枯枝,竟精准无比地钉入了瘦长男子眉心正中央!
力道之猛,竟让大半截树枝深深没入其颅骨之中!
瘦长男子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骇,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咕嚕,身体猛地一僵,前冲之势戛然而止。
眼中的神采,迅速黯淡、涣散,高大的身躯晃了晃,如同被抽去了所有骨头,软软地、沉重地向前扑倒在地,激起一片混著血水的泥泞。
至死,他都没看清那根树枝从何而来。
死寂!
庙內庙外,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只有哗啦啦的雨声,和篝火燃烧的噼啪声,显得格外刺耳。
所有目光,带著极致的震惊与茫然,齐刷刷地、僵硬地转向了那根夺命枯枝射来的方向——火堆旁,那个缓缓收回屈指轻弹动作的麻衣青年。
钟铭保持著格挡的姿势,长剑兀自横在身前,额角的冷汗混著雨水滑落,他瞪大的眼中充满了劫后余生的茫然与难以置信的震撼。
锦袍女子檀口微张,怀中的白猫也停止了呼嚕,金黄的猫瞳死死盯著倒地的尸体和那个平静的青年。
桐山双煞之一,凶名震慑镜州十数载的煞星,竟被一根隨手弹出的树枝……
轻易毙命?!
他哈哈一笑,举起手中那只粗陶小酒罈回敬:“公子好见识!此酒乃用上等三月杏……”
话音未落,
异变陡生!
“嗖!嗖!嗖——!”
一道悽厉的破空声撕裂雨幕,压过庙外轰隆的雷声,尖锐得令人头皮发麻!
紧接著,
便是数声短促而悽厉的惨嚎,如同被掐断喉咙的野兽,猛地灌入土庙。
眾人骇然望去,
只见原本守在庙门口的数名青衣汉子,如同被重锤击中,身躯剧震,踉蹌几步后,纷纷翻身栽倒在泥泞的门槛边。
冰冷的雨水冲刷著他们身上斜插而入的数支短小精悍、闪著幽蓝寒光的弩箭。
箭尾兀自震颤,血水混合著雨水,迅速在身下洇开。
“什么人?!”
钟铭与锦袍女子同时色变,惊喝出声。
钟铭反应快如闪电,
“沧啷——”一声,腰间长剑已然出鞘,寒光乍现,瞬间横在锦袍女子身前。
他双目如电扫向门外,厉声喝道:“护住小姐!!”
土庙內,其余青衣汉子虽惊不乱,训练有素的素质在此刻显现。
他们低吼一声,迅速收缩阵型,刀剑齐出,鏗鏘作响,顷刻间將钟铭与锦袍女子护在中间。
人人面色紧绷,紧盯著那洞开的、被风雨不断灌入的庙门。
另一边,
那李福全一家三口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血腥变故嚇得魂飞魄散。
妇人抱著孩子发出压抑的尖叫,男人李福全面无人色,连滚带爬地拖著妻儿,哭喊著缩向那尊残破神像之后,恨不得將身体嵌进冰冷的泥墙里。
“嗤拉——!”
又一道惨白的电蛇撕裂墨黑的苍穹,將破庙內外照得一片森然诡亮。
惨白的电光下,泥水横流,尸体伏地,兵刃寒光闪烁,映照著每一张惊惶或决绝的脸。
“嘿嘿嘿……”
一阵怪异、嘶哑,如同夜梟啼哭般的笑声,伴隨著沉重的脚步声,穿透雨幕,清晰地传入庙內。
电光再闪!
两道身影,一高一矮,已然无声无息地矗立在庙门之外,雨水顺著他们紧贴身体的黑色夜行衣流淌,倒是更添几分阴森。
高的那人,瘦长如竹,几乎比常人高出两头,面颊上赫然一块碗口大小、边缘狰狞的墨黑色胎记。
矮的那位,身高不过五六尺,身形佝僂得厉害,
然而其身后,竟斜背著一柄足有一人半高、刀身宽阔、刃口在电光下泛著冷冽青芒的巨型偃月刀。
“桐山双煞?!”
钟铭瞳孔骤然收缩,失声惊呼,握剑的手心瞬间沁出冷汗。
这二人,乃是十几年前镜州城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煞星!
凶名赫赫,犯下累累血案,手段残忍至极。
更可怕的是,这对兄弟皆是踏入后天境界多年的高手,一身横练功夫与诡异刀法配合无间,当年不知多少江湖好手摺在他们手下。
最终是镜州城几大势力联手围剿,付出不小代价才將这双魔头逐出镜州地界。
他们怎会在此刻出现?!
“嘿嘿嘿…”
那佝僂的矮个子怪笑几声,声音如同砂纸摩擦,他扭了扭脖子,发出咔吧脆响,
“想不到十几年过去,镜州城这腌臢地界,还有人记得我们兄弟的名头?”
他浑浊的小眼睛扫过钟铭,带著一丝扭曲的满意,“不错不错,你这小娃娃记性倒好,待会儿爷爷开恩,留你一个囫圇尸首!”
明明看上去年纪与钟铭相仿,却一口一个“小娃娃”、“爷爷”地叫著,其乖戾张狂之態,令人遍体生寒。
“大兄,其他杂鱼都给你消遣,”
那瘦长如竹竿的高个男子狞笑著接口,一双淫邪的眼珠却死死钉在角落锦袍女子那惊惧煞白的俏脸上,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十几年没开荤,都快忘了娘们儿是什么滋味了…这小娘子细皮嫩肉,归我了!”
话语中的污秽之意,让锦袍女子身边的健妇和丫鬟脸色惨白如纸,浑身发抖。
土庙之中,义安鏢局尚有二十余条精悍汉子,更有钟铭这等一流好手压阵。
可在这桐山双煞眼中,竟似视若无物一般。
“混帐!”
钟铭怒髮衝冠,厉声喝骂,心中却涌起惊涛骇浪,
“尔等魔头,十几年前已被各帮各派联手逐出镜州!如今怎敢回来?不怕再遭围剿,死无葬身之地?!”
“若不是那些大人物点了头,我们兄弟二人怎敢回来?真以为镜州城那些个什么江湖帮派就值得我们二人畏惧吗?”
那位身材佝僂的中年男子似是不屑的嗤笑一声,接著又慢悠悠的说道:
“放心,到时候不光你们义安鏢局,整个镜州城都要大变天的。”
“什么?!”
钟铭如遭雷击,心猛地沉入深渊。
他自幼在镜州城长大,半生心血都倾注在义安鏢局。
若桐山双煞所言非虚,那镜州城將迎来一场可怕的风暴,鏢局…危矣!
这消息带来的衝击,甚至比眼前的凶险更让他心如刀绞。
周围的青衣汉子们闻言,亦是面无人色,眼中流露出绝望。
“大变天么…”
火堆旁,魏凡依旧盘坐,仿佛置身事外,只是口中低不可闻地喃喃了一句,眼中若有所思,“看来这镜州城,果然不太平了。”
“大兄,何必跟这些將死之人废话!”
那瘦长高个早已按捺不住,眼中淫邪与杀意交织,“料理了他们,回城还有正事要做!”
话音未落,他佝僂矮小的大兄尚未动作,这瘦长身影却已如鬼魅般动了!
没有预兆,没有蓄力。
只见黑影一闪,那瘦长男子竟已越过数丈距离,无视挡在前方的眾多鏢师,如同瞬移般欺近到钟铭身前。
他右手两指併拢,指甲乌黑尖利,竟如毒蛇吐信,带著刺耳的锐啸,直插钟铭右侧太阳穴!
指尖未至,那阴冷的劲风已刺得钟铭太阳穴肌肤生疼!
太快了!
钟铭脑中一片空白,眼睁睁看著那双指如死亡之矛逼近,全身气力仿佛被瞬间抽空,连格挡的念头都来不及升起!
死亡的阴影瞬间將他笼罩。
“完了!”一个绝望的念头在他心中炸开。
然而,就在那乌黑指尖即將触及皮肤的剎那——
“嗖!”
一声轻微到几乎被雨声淹没的破空声响起。
一根寻常可见、拇指粗细、带著湿漉漉树皮的枯枝,如同被无形的弓弩射出,从庙內某个角落斜斜飞来。
它穿过混乱紧张的人群缝隙,轨跡刁钻无比,速度快逾闪电一般。
噗嗤!
一声轻响,如同石子投入烂泥。
那根枯枝,竟精准无比地钉入了瘦长男子眉心正中央!
力道之猛,竟让大半截树枝深深没入其颅骨之中!
瘦长男子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骇,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咕嚕,身体猛地一僵,前冲之势戛然而止。
眼中的神采,迅速黯淡、涣散,高大的身躯晃了晃,如同被抽去了所有骨头,软软地、沉重地向前扑倒在地,激起一片混著血水的泥泞。
至死,他都没看清那根树枝从何而来。
死寂!
庙內庙外,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只有哗啦啦的雨声,和篝火燃烧的噼啪声,显得格外刺耳。
所有目光,带著极致的震惊与茫然,齐刷刷地、僵硬地转向了那根夺命枯枝射来的方向——火堆旁,那个缓缓收回屈指轻弹动作的麻衣青年。
钟铭保持著格挡的姿势,长剑兀自横在身前,额角的冷汗混著雨水滑落,他瞪大的眼中充满了劫后余生的茫然与难以置信的震撼。
锦袍女子檀口微张,怀中的白猫也停止了呼嚕,金黄的猫瞳死死盯著倒地的尸体和那个平静的青年。
桐山双煞之一,凶名震慑镜州十数载的煞星,竟被一根隨手弹出的树枝……
轻易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