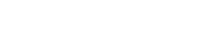第153章 牛憨:这个妹妹我好像认得!
蹇硕绝非庸碌之辈。
他能在诡譎莫测的深宫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权势不逊於十常侍的大太监,自有其一套立身存命的法则。
这位陛下长女,平日里深居简出,看似与其他公主无异,只在宫中陪伴太妃,侍奉父皇母后,一副温良嫻静的模样。
可蹇硕在宫中沉浮多年,深知天家无庸人,越是这般看似与世无爭的,越是需要警惕。
几件旧事浮上心头。
去年陛下曾有意將乐安公主许配给某位朝中重臣之子,意在笼络。
这风声才传出不过数日,那位重便因一桩陈年旧案遭御史台联名弹劾。
隨后便被陛下一路贬至交州,去那蛮荒之地担任刺史去了。
而联姻之事,陛下自然也再未提起过。
还有那次,宫中一位风头正盛的美人,因琐事欲惩处乐安公主生母杜贵人旧宫中的侍女。
不出三日,那美人的胞弟便在宫外惹上大麻烦,不仅丟了差事,连性命都是那位美人在陛下宫门外跪了一整天才勉强保住。
自那以后,那位美人再见乐安公主时,再不敢有半分造次。
再加上这次的“祥瑞”之事————
她借著这股东风,不仅敲打了张让、赵忠二人,卖了卢植那老傢伙一个人情,更从陛下手中拿到了乐安国的任免之权!
往日只当是巧合,或是京兆杜氏余荫犹存。如今將这些蛛丝马跡串联起来——————
蹇硕想到此处,不由的打了个冷战。
若这些事当真是这位乐安公主一手谋划,那她的心机手段,未免太过可怕!
他看了一眼地上碎裂的玉杯,心中凛然。
东莱贡品虽好,但为了这点財物,贸然与一个看不清深浅的公主正面衝突,绝非明智之举。
更何况—
“那周正,不过是公主府一家令,就敢公然驳咱家的面子,大开中门迎那群东莱武夫入府。”
“若无公主授意或默许,他岂有这般胆量?”
蹇硕眯起眼睛,细细揣摩其中关节,“公主此举,分明是在告诉咱家,这东莱使团,她保定了!”
他踱至窗边,望向皇宫方向。夜色中的宫闕楼宇,如蛰伏的巨兽,静默而危险。
“是了,她如今刚刚得了封地的任免权,正是需要立威之时!”
蹇硕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在宫中单打独斗的常侍,倒成了最合適的靶子—
宦官出身,人人喊打,没什么根基,与十常侍相交不深,甚至还有些旧怨————
“咱家若此刻撞上去,岂不是自討苦吃?”
想到这一层,蹇硕彻底熄了立刻对贡品下手的心思。
“罢了,”他挥了挥手,语气中带著不甘却又无奈,”传话下去,让下面的人都安分些,暂时不要去招惹东莱使团,尤其是那个牛憨。”
“公主府那边————也先別去碰。”
“那————贡品的事?”手下小心翼翼地问道。
“贡品?”蹇硕冷哼一声,“既然已经进了公主府的地盘,再动手就是打公主的脸了。”
“再说,咱家难道还缺那穷乡僻壤的一份供奉?”
“更何况,”他语气微顿,带著几分自得:“无论那刘玄德献上多少財宝,那里头,总归有咱家的一份功劳!”
与此同时,深宫之中,兰林苑內。
乐安公主刘疏君正对镜卸妆,听完了周正的稟报。
她执起玉梳的手微微一顿,清冷的眸子里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
“倒是比我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直接些。”
她对著镜中自己绝美的容顏,轻声自语。
“周正。”
“臣在。”
“府里,好生照看著。一应用度,不可短缺。至於蹇硕那边————”
她语气平淡,“他是聪明人,自然不会再来聒噪。”
“臣,明白。”周正躬身应道。隨后犹豫半响,又问:“殿下可要召见?臣见东莱副使一表人才————”
“不急。”刘疏君放下玉梳,青丝如瀑垂落腰际,“此时召见,太过刻意。他们甫一入京便闹出这般动静,此刻不知多少双眼睛盯著。”
“让他们在府中好生休整几日,待风浪稍平,再见不迟。”
她起身,缓步走向窗边,望向兰林苑中在夜色下摇曳的疏竹。
“况且,本宫也想看看,这牛憨,是真憨直,还是大智若愚;”
“那诸葛珪,是明珠,还是鱼目。”
“蹇硕虽暂时退去,但朝中贪慾熏天的,又不止他一人!接下来几日,洛阳城里,想必不会无聊。”
周正垂首:“殿下深谋远虑。只是————那贡品?”
“既是献给父皇的祥瑞,自然要好生送到父皇面前。”
刘疏君唇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不过,如何送,何时送,由谁送,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小。蹇硕想截胡,本宫偏要让它风风光光,人尽皆知地送入宫中。”
周正心领神会:“臣明白。定会办得妥帖,不留痕跡。”
“嗯。”刘疏君轻轻頷首,”去吧。府中之事,你多费心。”
“那牛憨与诸葛珪,若有任何需求,只要不过分,儘量满足。”
“特別是那诸葛珪,观其言行,似是读书明理之人,可让府中典籍官寻个由头,允他查阅府中藏书。”
“殿下是想————?”
“人才难得。纵不能为我所用,结个善缘也是好的。”
刘疏君语气平淡,目光却依旧停留在窗外幽深的夜色中:“这盘棋才刚刚开始,多一枚棋子,便多一分胜算。”
“臣,谨遵殿下吩咐。”周正深深一揖,悄然退下。
寢殿內重归寂静,只余灯花偶尔爆开的轻微啪声。
刘疏君独立窗前,指尖轻轻划过冰凉的窗欞。
“东莱————刘玄德————卢植————”
她低声咀嚼著这几个名字,“能让卢尚书如此回护,为你这弟子扫清隱患,刘玄德,你究竟是何等人物?”
“还有这牛憨,看似鲁莽,却能在蹇硕的逼迫下,想到直闯公主府这步险棋,”
“是误打误撞,还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她沉思片刻,微微摇头。
“无论如何,棋子既已落盘,便没有回头路了。”
“父皇————希望我这后手最好用不到吧————”
在公主府西跨院安顿下来的这几日,堪称东莱使节团入京以来最为舒心安稳的时光。
诸葛珪终日流连於府中藏书阁,捧著一卷《古文尚书》如获至宝,读得如痴如醉。
牛憨依旧雷打不动地早起练斧。
因傅士仁住处离他颇近,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固定陪练。
每日天光未亮,牛憨便准时將他唤起。
如今傅士仁已渐渐摸清了牛憨的路数,在其刻意收著力道的情况下,两人已能你来我往地过上七八招了。
故而虽然每日早起非常痛苦,但傅士仁还是乐在其中。
不过毕竟是进京献贡的队伍,正事还是要做的。
这日,公主家令周正,便传来消息。
——
言道公主殿下將於午后在府中水榭召见。
消息传来,诸葛珪立刻整理衣冠,反覆推敲覲见时的言辞。
牛憨则依旧如常,只是在傅士仁的提醒下,换上了一身乾净些的军袍,那柄门板似的巨斧却依旧不离身。
午后,二人跟隨引路的侍女,穿过重重回廊,来到府邸深处的一处临湖水榭。
水榭四面通透,轻纱曼舞,窗外湖光瀲灩,偶有游鱼跃出水面,激起圈圈涟漪。
一位身著素雅宫装以轻纱遮面的女子正凭栏而立,身姿挺拔,气质清冷如兰。
她身侧侍立著两名侍女,一人高挑劲装,眉宇间带著英气;另一人娇小活泼,眼神灵动。
“东莱郡副使诸葛珪,拜见公主殿下。”
“东莱郡忠勇校尉牛憨,拜见公主殿下。”
诸葛珪率先躬身行礼,言辞恭谨。
牛憨也跟著抱拳,声音洪亮。
乐安公主刘疏君缓缓转过身,目光如水,掠过诸葛珪,最终落在了牛憨身上。
不过她並未立即让二人起身,而是仿佛在思考著什么。
水榭中一时间只闻风吹纱幔的细微声响。
牛憨等了半天,不见公主说话,心中纳闷,於是抬头看去。
他的目光先是扫过公主,然后又扫过公主身侧那位高挑劲装的侍女。
最后落在那娇小活泼的侍女身上。
奇怪。
有些眼熟。
牛憨抓抓脑袋,又將视线转移到公主身侧那位高挑劲装的侍女身上。
那眉眼,那利落的身形,还有那种感觉————
唉?
哎!
牛憨铜铃般的眼睛一点点瞪大,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哎!
他伸出一根粗壮的手指,指著秋水。
唉?哎!!
隨后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下乐安公主,嘴巴张了张,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哎最后才像是终於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带著巨大的震惊和茫然,瓮声瓮气地脱口而出:“你——你——你不是那个——河边——捞俺上来的——公子吗?!”
“还有你!”他又指向秋水,“你不是那个——力气挺大——捞俺又捞斧子的——姑娘吗?!”
“你们是公主?!”
他这番举动,已经全然忘记了礼数,巨大的嗓门震得水榭仿佛都晃了晃。
诸葛珪在一旁听得冷汗直流,拽著牛憨袖子急忙低声提醒:“四將军!礼节!”
不过他一个文士,哪里能控制的住牛憨那大力?
反而被牛憨抖动著指向秋水的右手带了一个跟蹌。
险些站之不住。
而刘疏君则被牛憨这突如其来的惊呼弄得微微一怔,隨即,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漾开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憨子居然有这般有趣的反应。
她並未否认,只是淡淡开口,声音依旧带著那份独特的冷澈:“牛国丞,洛水一別,別来无恙?”
这便是承认了!
牛憨得到確认,脸上的震惊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又添加了一丝疑惑。
脑子里仿佛有无数个线团搅在一起,完全理不清头绪。
他想不明白,那个在河边凉亭里说话带刺、却又好心救他、还帮他捞斧子的“公子”,怎么就变成了眼前这位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
“那日渭水之畔,不过是本宫一时兴起,微服出游,恰逢其会罢了。”
刘疏君轻描淡写地將那日的惊险一语带过,但隨后语气带著一丝少见的挪移,让一旁偷笑的冬桃都忍不住侧目:“倒是牛校尉你,以后走路多看看脚下。”
牛憨这才慢慢回过神来,脑子里那点有限的智慧终於开始转动,“俺——俺——”他“俺”了半天,也没“俺”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憋出一句,“谢谢你上次救俺!”
这番憨直的反应,顿时让水榭中顿时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
冬桃忍笑忍得辛苦,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诸葛珪以手扶额,简直不忍直视。
不过这样倒是反而衝散了水榭中原本有些严肃的气氛,刘疏君眼底闪过一丝无奈,摆了摆手打发正笑憋的辛苦的冬桃前去请茶:“些许小事,不必掛齿。牛国丞,诸葛先生,请坐吧。”
待二人落座,冬桃奉上香茗,氤氳热气方才裊裊升起,谈话也隨之转入正题。
公主既已施以庇护,诸葛珪自是心领神会,不敢怠慢。
不待刘疏君安坐片刻,他便已自袖中取出一卷绢帛,双手奉上—一正是东莱贡品的详细清单。
秋水上前接过,转呈至公主案前。
刘疏君素手轻抬,將那捲绢帛徐徐展开,目光自上而下,淡然扫过。
她身为大汉长公主,自幼长於深宫,母妃出身京兆杜氏嫡系,虽已故去,杜家仍按旧例,年年將份例送入宫中,从无短缺。
什么金玉珠翠、海外奇珍,於她而言,不过是宫苑日常,早已见惯。
故她自认为,此刻览此清单,心中应该是波澜不惊。
但没想到。
起初,她的神色还算平静,但隨著看到的物品名称和数量越来越多,她那执卷的纤指微微顿住,平静无波的眸子里终於掠过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诧。
“蜀锦万匹,赤金千斤,东海明珠百斛,血玉珊瑚十只,鎏金羽人像————”
初步估算————
这价值,少说也要一亿钱!!!
她抬起眼,看向诸葛珪,语气中带著一丝难以置信的迷茫:“诸葛先生,这清单上所列————”
“皆是刘太守欲献於父皇的?”
说著,她那时长清冷如玉的语气变得严肃:“他————他搜刮民脂民膏了???”
>
蹇硕绝非庸碌之辈。
他能在诡譎莫测的深宫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权势不逊於十常侍的大太监,自有其一套立身存命的法则。
这位陛下长女,平日里深居简出,看似与其他公主无异,只在宫中陪伴太妃,侍奉父皇母后,一副温良嫻静的模样。
可蹇硕在宫中沉浮多年,深知天家无庸人,越是这般看似与世无爭的,越是需要警惕。
几件旧事浮上心头。
去年陛下曾有意將乐安公主许配给某位朝中重臣之子,意在笼络。
这风声才传出不过数日,那位重便因一桩陈年旧案遭御史台联名弹劾。
隨后便被陛下一路贬至交州,去那蛮荒之地担任刺史去了。
而联姻之事,陛下自然也再未提起过。
还有那次,宫中一位风头正盛的美人,因琐事欲惩处乐安公主生母杜贵人旧宫中的侍女。
不出三日,那美人的胞弟便在宫外惹上大麻烦,不仅丟了差事,连性命都是那位美人在陛下宫门外跪了一整天才勉强保住。
自那以后,那位美人再见乐安公主时,再不敢有半分造次。
再加上这次的“祥瑞”之事————
她借著这股东风,不仅敲打了张让、赵忠二人,卖了卢植那老傢伙一个人情,更从陛下手中拿到了乐安国的任免之权!
往日只当是巧合,或是京兆杜氏余荫犹存。如今將这些蛛丝马跡串联起来——————
蹇硕想到此处,不由的打了个冷战。
若这些事当真是这位乐安公主一手谋划,那她的心机手段,未免太过可怕!
他看了一眼地上碎裂的玉杯,心中凛然。
东莱贡品虽好,但为了这点財物,贸然与一个看不清深浅的公主正面衝突,绝非明智之举。
更何况—
“那周正,不过是公主府一家令,就敢公然驳咱家的面子,大开中门迎那群东莱武夫入府。”
“若无公主授意或默许,他岂有这般胆量?”
蹇硕眯起眼睛,细细揣摩其中关节,“公主此举,分明是在告诉咱家,这东莱使团,她保定了!”
他踱至窗边,望向皇宫方向。夜色中的宫闕楼宇,如蛰伏的巨兽,静默而危险。
“是了,她如今刚刚得了封地的任免权,正是需要立威之时!”
蹇硕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在宫中单打独斗的常侍,倒成了最合適的靶子—
宦官出身,人人喊打,没什么根基,与十常侍相交不深,甚至还有些旧怨————
“咱家若此刻撞上去,岂不是自討苦吃?”
想到这一层,蹇硕彻底熄了立刻对贡品下手的心思。
“罢了,”他挥了挥手,语气中带著不甘却又无奈,”传话下去,让下面的人都安分些,暂时不要去招惹东莱使团,尤其是那个牛憨。”
“公主府那边————也先別去碰。”
“那————贡品的事?”手下小心翼翼地问道。
“贡品?”蹇硕冷哼一声,“既然已经进了公主府的地盘,再动手就是打公主的脸了。”
“再说,咱家难道还缺那穷乡僻壤的一份供奉?”
“更何况,”他语气微顿,带著几分自得:“无论那刘玄德献上多少財宝,那里头,总归有咱家的一份功劳!”
与此同时,深宫之中,兰林苑內。
乐安公主刘疏君正对镜卸妆,听完了周正的稟报。
她执起玉梳的手微微一顿,清冷的眸子里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
“倒是比我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直接些。”
她对著镜中自己绝美的容顏,轻声自语。
“周正。”
“臣在。”
“府里,好生照看著。一应用度,不可短缺。至於蹇硕那边————”
她语气平淡,“他是聪明人,自然不会再来聒噪。”
“臣,明白。”周正躬身应道。隨后犹豫半响,又问:“殿下可要召见?臣见东莱副使一表人才————”
“不急。”刘疏君放下玉梳,青丝如瀑垂落腰际,“此时召见,太过刻意。他们甫一入京便闹出这般动静,此刻不知多少双眼睛盯著。”
“让他们在府中好生休整几日,待风浪稍平,再见不迟。”
她起身,缓步走向窗边,望向兰林苑中在夜色下摇曳的疏竹。
“况且,本宫也想看看,这牛憨,是真憨直,还是大智若愚;”
“那诸葛珪,是明珠,还是鱼目。”
“蹇硕虽暂时退去,但朝中贪慾熏天的,又不止他一人!接下来几日,洛阳城里,想必不会无聊。”
周正垂首:“殿下深谋远虑。只是————那贡品?”
“既是献给父皇的祥瑞,自然要好生送到父皇面前。”
刘疏君唇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不过,如何送,何时送,由谁送,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小。蹇硕想截胡,本宫偏要让它风风光光,人尽皆知地送入宫中。”
周正心领神会:“臣明白。定会办得妥帖,不留痕跡。”
“嗯。”刘疏君轻轻頷首,”去吧。府中之事,你多费心。”
“那牛憨与诸葛珪,若有任何需求,只要不过分,儘量满足。”
“特別是那诸葛珪,观其言行,似是读书明理之人,可让府中典籍官寻个由头,允他查阅府中藏书。”
“殿下是想————?”
“人才难得。纵不能为我所用,结个善缘也是好的。”
刘疏君语气平淡,目光却依旧停留在窗外幽深的夜色中:“这盘棋才刚刚开始,多一枚棋子,便多一分胜算。”
“臣,谨遵殿下吩咐。”周正深深一揖,悄然退下。
寢殿內重归寂静,只余灯花偶尔爆开的轻微啪声。
刘疏君独立窗前,指尖轻轻划过冰凉的窗欞。
“东莱————刘玄德————卢植————”
她低声咀嚼著这几个名字,“能让卢尚书如此回护,为你这弟子扫清隱患,刘玄德,你究竟是何等人物?”
“还有这牛憨,看似鲁莽,却能在蹇硕的逼迫下,想到直闯公主府这步险棋,”
“是误打误撞,还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她沉思片刻,微微摇头。
“无论如何,棋子既已落盘,便没有回头路了。”
“父皇————希望我这后手最好用不到吧————”
在公主府西跨院安顿下来的这几日,堪称东莱使节团入京以来最为舒心安稳的时光。
诸葛珪终日流连於府中藏书阁,捧著一卷《古文尚书》如获至宝,读得如痴如醉。
牛憨依旧雷打不动地早起练斧。
因傅士仁住处离他颇近,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固定陪练。
每日天光未亮,牛憨便准时將他唤起。
如今傅士仁已渐渐摸清了牛憨的路数,在其刻意收著力道的情况下,两人已能你来我往地过上七八招了。
故而虽然每日早起非常痛苦,但傅士仁还是乐在其中。
不过毕竟是进京献贡的队伍,正事还是要做的。
这日,公主家令周正,便传来消息。
——
言道公主殿下將於午后在府中水榭召见。
消息传来,诸葛珪立刻整理衣冠,反覆推敲覲见时的言辞。
牛憨则依旧如常,只是在傅士仁的提醒下,换上了一身乾净些的军袍,那柄门板似的巨斧却依旧不离身。
午后,二人跟隨引路的侍女,穿过重重回廊,来到府邸深处的一处临湖水榭。
水榭四面通透,轻纱曼舞,窗外湖光瀲灩,偶有游鱼跃出水面,激起圈圈涟漪。
一位身著素雅宫装以轻纱遮面的女子正凭栏而立,身姿挺拔,气质清冷如兰。
她身侧侍立著两名侍女,一人高挑劲装,眉宇间带著英气;另一人娇小活泼,眼神灵动。
“东莱郡副使诸葛珪,拜见公主殿下。”
“东莱郡忠勇校尉牛憨,拜见公主殿下。”
诸葛珪率先躬身行礼,言辞恭谨。
牛憨也跟著抱拳,声音洪亮。
乐安公主刘疏君缓缓转过身,目光如水,掠过诸葛珪,最终落在了牛憨身上。
不过她並未立即让二人起身,而是仿佛在思考著什么。
水榭中一时间只闻风吹纱幔的细微声响。
牛憨等了半天,不见公主说话,心中纳闷,於是抬头看去。
他的目光先是扫过公主,然后又扫过公主身侧那位高挑劲装的侍女。
最后落在那娇小活泼的侍女身上。
奇怪。
有些眼熟。
牛憨抓抓脑袋,又將视线转移到公主身侧那位高挑劲装的侍女身上。
那眉眼,那利落的身形,还有那种感觉————
唉?
哎!
牛憨铜铃般的眼睛一点点瞪大,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哎!
他伸出一根粗壮的手指,指著秋水。
唉?哎!!
隨后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下乐安公主,嘴巴张了张,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哎最后才像是终於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带著巨大的震惊和茫然,瓮声瓮气地脱口而出:“你——你——你不是那个——河边——捞俺上来的——公子吗?!”
“还有你!”他又指向秋水,“你不是那个——力气挺大——捞俺又捞斧子的——姑娘吗?!”
“你们是公主?!”
他这番举动,已经全然忘记了礼数,巨大的嗓门震得水榭仿佛都晃了晃。
诸葛珪在一旁听得冷汗直流,拽著牛憨袖子急忙低声提醒:“四將军!礼节!”
不过他一个文士,哪里能控制的住牛憨那大力?
反而被牛憨抖动著指向秋水的右手带了一个跟蹌。
险些站之不住。
而刘疏君则被牛憨这突如其来的惊呼弄得微微一怔,隨即,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漾开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憨子居然有这般有趣的反应。
她並未否认,只是淡淡开口,声音依旧带著那份独特的冷澈:“牛国丞,洛水一別,別来无恙?”
这便是承认了!
牛憨得到確认,脸上的震惊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又添加了一丝疑惑。
脑子里仿佛有无数个线团搅在一起,完全理不清头绪。
他想不明白,那个在河边凉亭里说话带刺、却又好心救他、还帮他捞斧子的“公子”,怎么就变成了眼前这位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
“那日渭水之畔,不过是本宫一时兴起,微服出游,恰逢其会罢了。”
刘疏君轻描淡写地將那日的惊险一语带过,但隨后语气带著一丝少见的挪移,让一旁偷笑的冬桃都忍不住侧目:“倒是牛校尉你,以后走路多看看脚下。”
牛憨这才慢慢回过神来,脑子里那点有限的智慧终於开始转动,“俺——俺——”他“俺”了半天,也没“俺”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憋出一句,“谢谢你上次救俺!”
这番憨直的反应,顿时让水榭中顿时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
冬桃忍笑忍得辛苦,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诸葛珪以手扶额,简直不忍直视。
不过这样倒是反而衝散了水榭中原本有些严肃的气氛,刘疏君眼底闪过一丝无奈,摆了摆手打发正笑憋的辛苦的冬桃前去请茶:“些许小事,不必掛齿。牛国丞,诸葛先生,请坐吧。”
待二人落座,冬桃奉上香茗,氤氳热气方才裊裊升起,谈话也隨之转入正题。
公主既已施以庇护,诸葛珪自是心领神会,不敢怠慢。
不待刘疏君安坐片刻,他便已自袖中取出一卷绢帛,双手奉上—一正是东莱贡品的详细清单。
秋水上前接过,转呈至公主案前。
刘疏君素手轻抬,將那捲绢帛徐徐展开,目光自上而下,淡然扫过。
她身为大汉长公主,自幼长於深宫,母妃出身京兆杜氏嫡系,虽已故去,杜家仍按旧例,年年將份例送入宫中,从无短缺。
什么金玉珠翠、海外奇珍,於她而言,不过是宫苑日常,早已见惯。
故她自认为,此刻览此清单,心中应该是波澜不惊。
但没想到。
起初,她的神色还算平静,但隨著看到的物品名称和数量越来越多,她那执卷的纤指微微顿住,平静无波的眸子里终於掠过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诧。
“蜀锦万匹,赤金千斤,东海明珠百斛,血玉珊瑚十只,鎏金羽人像————”
初步估算————
这价值,少说也要一亿钱!!!
她抬起眼,看向诸葛珪,语气中带著一丝难以置信的迷茫:“诸葛先生,这清单上所列————”
“皆是刘太守欲献於父皇的?”
说著,她那时长清冷如玉的语气变得严肃:“他————他搜刮民脂民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