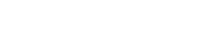东海。
浪头拍在“镇海”號的龙骨上,发出重锤敲鼓似的闷响。
这艘大明最庞大的宝船,现在跑起来很不痛快。
它不是没风,是太沉了。
那是从船心儿里透出来的沉。
几千万两银子压在舱底,入水极深。
原本那些画在船舷上的吃水线,早就钻进水里,甚至连那层滑腻腻的暗绿海藻都快要亲到甲板边缘。
“嘎吱——嘎吱——”
每一块老红木甲板都在哀嚎。
底下塞的不是货,是大明未来几十年的国命,是能把金陵城地皮都厚厚铺上一层白银的底气。
旗舰三楼,那个为了承重特意加固三层的露台上。
朱高炽陷在特製的摇椅里,整个人瘫成一团软面。
在倭国这半年,他別的没学会,这“敲骨吸髓”的艺术倒是无师自通。
他现在胖得很有章法。
呼一口气,肚皮上那几层狐裘掩盖的肉褶子,都能跟著海浪的节奏来回晃悠。
“殿下,风硬了,奴婢给您披实点?”
左侧倭女细声细气。
她是大內氏精心挑出来的宗室血脉,跪在那儿的姿势卑微到骨子里。
但在朱高炽眼里,这跟家里揉面的厨娘没两样。
“別动,让我歇会儿。”
朱高炽费劲地摆摆手。
他那双被肥肉挤得快找不著的缝眼,盯著手里那串葡萄。
这玩意儿在倭国是稀罕货,酸得倒牙,但他吃得最是有劲。
因为这葡萄一斤要卖十两银子。
卖给谁?
卖给那些在地底下玩命挖矿的倭国旧贵族。
“老觉得大堂哥在背后盯著我。”
“不是盯著,是那种……要把我这身肥肉都给算计成银子的味儿。”
朱高炽嘀咕一句。
他顺手抓起案几上的烧鸡。
这是石见总督府的大厨拿手戏,皮儿酥得一碰就碎,油汪汪的招人疼。
他扯下一只鸡腿,嘴巴一吸,光禿禿的骨头就飞出来。
还没等他咽下去。
海浪一个猛烈的顛簸。
朱高炽脸上的血色刷的一下撤了个乾净,先是白得跟纸糊的一样,紧接著就开始泛青。
他扶著特製的扶手,整个人直接瘫在船舷上。
“哇——”
刚才那根金贵的鸡腿,连同他在石见攒下的那点酒气,一股脑吐进东海,全餵鱼。
“殿下,您这肠胃,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您留。”
蓝春冷不丁冒出来。
这位凉国公的大公子,现在皮肤黑得发亮,分明是在炭火里滚过一圈的模样。
他那一身板甲擦得鋥亮,腰间挎著的佩刀隨著走路叮噹作响。
这种动静,是大明新式军官最狂热的节奏。
“帕子。”
蓝春隨手甩过一块浸冰水的冷帕。
蓝斌跟在后头,手里还拿著那个真皮包边的单筒望远镜。
“春哥儿,我就说世子爷这病没治。”
蓝斌笑出声,这语气里全是战场上磨出来的铁瓷味儿,没那么多尊卑客套。
“他在岛上这半年,算帐比谁都凶,吃肉比谁都快。”
“我看那石见银山的產出,起码得有十万两,变成了他肚皮上这身膘。”
朱高炽擦了把嘴,虚晃著指了指蓝斌,嗓子眼还在发酸。
“你们……懂个屁。”
“我这是……为国分忧。”
“你知道大堂哥给我的那个算盘,珠子都快打飞了吗?”
朱高炽吃力地直起腰。
摇椅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惨叫,眼看著就要塌。
“蓝大將军,你们杀人那是力气活。”
“我这动脑子的,才是耗损阳寿。”
他指了指脚底下。
“这舱底下的银子,每一两上头都刻著我朱高炽流过的冷汗。”
提到了钱,朱高炽眼中绿光大盛,连晕船的劲头都给压下去三分。
“咱们这趟,到底带回来多少?”
蓝春压低嗓门。
饶是带兵的杀才,问及此事也喉头髮紧。
他是统帅,只负责把倭人撵进矿坑。
至於最后到底掏出多少宝贝,那是朱高炽一个人的绝对机密。
朱高炽没吭声。
他从怀里摸出一把纯金打的小算盘,只有巴掌大。
手指在金珠子上隨意一拨。
那动静,清脆得能勾掉人的魂儿。
“这响动,不比秦淮河那些小调好听?”
朱高炽又抓起一块魷鱼丝塞嘴里,整个人透著股守財奴的亢奋。
“给你们交个实底。”
“听好了,別嚇得直接掉海里。”
“金子,纯度最高的,一百二十万两。”
“白银,按照大堂哥要求的法子提炼的顶级料子……八千万两。”
“咣当!”
蓝斌手里的望远镜直接砸在甲板上。
这位在山口城面对万军衝锋都没皱眉的小將,眼珠子瞪得滚圆。
“多……多少?”
“八千万两白银?”
蓝斌挨了好大一记闷棍。
“世子,你这手……没抖?没多拨几个零?”
“咱们大明这一年的岁入统共才几个钱?”
“你这一船,带回咱们三十年的国库?”
朱高炽撇了撇嘴,一脸的这种“格局打开”的表情。
“土包子。”
“这还没算山口城码头那一座座铜山。”
“你们那是杀得爽了,我是抄家抄到手软。”
“足利义满那个老鬼,把扶桑积攒千年的財富都搂进自己怀里。”
“一把火烧御所有个屁用?金子在土底下,它烧不化啊!”
朱高炽哼唧两声。
“我带著大內义弘那个老瘸子,挨家挨户敲门。”
“我说,大明天军帮你们清叛党,这是公道。”
“帮你们名正言顺,这是大恩。”
“既然有恩有德,你们这些大名、地主,是不是得拿点钱,给天军兄弟们买两件御寒的冬衣?”
朱高炽笑得一脸憨厚。
但在蓝春眼里,这笑容比他老子蓝玉的刀还狠,还毒。
“谁敢不给?”
“不给就是藐视朝廷,那就是足利余孽。”
“蓝大將军,你那神机营的枪子儿,可不是摆设。”
蓝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虚汗。
他看向远处那一望无际、吃水极深的庞大船队。
九艘大宝船,三十多艘副舰。
每一根桅杆都绷到极限。
那是泼天財富的重量。
“世子,末將这心里……发虚。”
蓝春看著朱高炽,语调都变了。
“以前我觉得,刀快就能打天下。”
“现在看这舱底,这世道,变了样。”
朱高炽咽下魷鱼丝。
他拍了拍那身松垮的袍子,目光看向遥远的北方。
那是大明金陵。
“大堂哥说过,这世上的道理,一半在炮管子里,另一半……就在这白银的成色里。”
“这一亿两,就是大明的骨头。”
朱高炽费劲地弯腰。
“我是想看看大堂哥的脸。”
“那人向来把一切摸得透透的,什么都算在前面。”
“这次,我要把这一亿两银子,一箱一箱地砸在他脚底下。”
“我得让他明白,打仗我確实不成;但论起搞钱,他得管我叫声祖宗!”
朱高炽越说越来劲,胖脸上的肉一顛一顛的。
他胸口堵著一股气。
在应天府被碾压智商,在船上吐一路丟脸面,全得在这一笔钱上挣回来。
这一亿两,就是他朱高炽挺起腰杆的本钱。
“蓝春,你说,要是咱们把银子拉进城,把御道都给铺平了,大堂哥会不会气得跳脚?”
蓝春尷尬地笑了笑,这问题他实在不敢接。
……
东海,大明海域。
原本翻涌的浊浪,撞上这支由钢铁巨舰组成的船队,也缓势头。
旗舰“镇海”號上。
瞭望员紧攥著黄铜望远镜,手心全是汗。
由於死盯海平线,他的眼眶早就烧得发红,但他不敢眨眼。
镜头里,那抹模糊的黛青色,正一点点变得清晰,变得稳固。
那不是雾,是陆地。
是那条被大明匠人修整过无数次的,代表家园的海岸线。
“陆地!!”
“看见陆地了!!”
“大明——!!我们回来啦!!”
尖叫声穿透海风,响彻甲板。
静止了。
镇海號上一下没了声响。
正准备换班的水手扔掉缆绳,顾不得手心的血泡,疯似的往船舷边冲。
正在舱底检查银球的甲士,不顾闷热,连滚带爬地顺著木梯往上钻。
万眾齐声吶喊。
“万胜——!!”
“大明万胜——!!”
浪头拍在“镇海”號的龙骨上,发出重锤敲鼓似的闷响。
这艘大明最庞大的宝船,现在跑起来很不痛快。
它不是没风,是太沉了。
那是从船心儿里透出来的沉。
几千万两银子压在舱底,入水极深。
原本那些画在船舷上的吃水线,早就钻进水里,甚至连那层滑腻腻的暗绿海藻都快要亲到甲板边缘。
“嘎吱——嘎吱——”
每一块老红木甲板都在哀嚎。
底下塞的不是货,是大明未来几十年的国命,是能把金陵城地皮都厚厚铺上一层白银的底气。
旗舰三楼,那个为了承重特意加固三层的露台上。
朱高炽陷在特製的摇椅里,整个人瘫成一团软面。
在倭国这半年,他別的没学会,这“敲骨吸髓”的艺术倒是无师自通。
他现在胖得很有章法。
呼一口气,肚皮上那几层狐裘掩盖的肉褶子,都能跟著海浪的节奏来回晃悠。
“殿下,风硬了,奴婢给您披实点?”
左侧倭女细声细气。
她是大內氏精心挑出来的宗室血脉,跪在那儿的姿势卑微到骨子里。
但在朱高炽眼里,这跟家里揉面的厨娘没两样。
“別动,让我歇会儿。”
朱高炽费劲地摆摆手。
他那双被肥肉挤得快找不著的缝眼,盯著手里那串葡萄。
这玩意儿在倭国是稀罕货,酸得倒牙,但他吃得最是有劲。
因为这葡萄一斤要卖十两银子。
卖给谁?
卖给那些在地底下玩命挖矿的倭国旧贵族。
“老觉得大堂哥在背后盯著我。”
“不是盯著,是那种……要把我这身肥肉都给算计成银子的味儿。”
朱高炽嘀咕一句。
他顺手抓起案几上的烧鸡。
这是石见总督府的大厨拿手戏,皮儿酥得一碰就碎,油汪汪的招人疼。
他扯下一只鸡腿,嘴巴一吸,光禿禿的骨头就飞出来。
还没等他咽下去。
海浪一个猛烈的顛簸。
朱高炽脸上的血色刷的一下撤了个乾净,先是白得跟纸糊的一样,紧接著就开始泛青。
他扶著特製的扶手,整个人直接瘫在船舷上。
“哇——”
刚才那根金贵的鸡腿,连同他在石见攒下的那点酒气,一股脑吐进东海,全餵鱼。
“殿下,您这肠胃,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您留。”
蓝春冷不丁冒出来。
这位凉国公的大公子,现在皮肤黑得发亮,分明是在炭火里滚过一圈的模样。
他那一身板甲擦得鋥亮,腰间挎著的佩刀隨著走路叮噹作响。
这种动静,是大明新式军官最狂热的节奏。
“帕子。”
蓝春隨手甩过一块浸冰水的冷帕。
蓝斌跟在后头,手里还拿著那个真皮包边的单筒望远镜。
“春哥儿,我就说世子爷这病没治。”
蓝斌笑出声,这语气里全是战场上磨出来的铁瓷味儿,没那么多尊卑客套。
“他在岛上这半年,算帐比谁都凶,吃肉比谁都快。”
“我看那石见银山的產出,起码得有十万两,变成了他肚皮上这身膘。”
朱高炽擦了把嘴,虚晃著指了指蓝斌,嗓子眼还在发酸。
“你们……懂个屁。”
“我这是……为国分忧。”
“你知道大堂哥给我的那个算盘,珠子都快打飞了吗?”
朱高炽吃力地直起腰。
摇椅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惨叫,眼看著就要塌。
“蓝大將军,你们杀人那是力气活。”
“我这动脑子的,才是耗损阳寿。”
他指了指脚底下。
“这舱底下的银子,每一两上头都刻著我朱高炽流过的冷汗。”
提到了钱,朱高炽眼中绿光大盛,连晕船的劲头都给压下去三分。
“咱们这趟,到底带回来多少?”
蓝春压低嗓门。
饶是带兵的杀才,问及此事也喉头髮紧。
他是统帅,只负责把倭人撵进矿坑。
至於最后到底掏出多少宝贝,那是朱高炽一个人的绝对机密。
朱高炽没吭声。
他从怀里摸出一把纯金打的小算盘,只有巴掌大。
手指在金珠子上隨意一拨。
那动静,清脆得能勾掉人的魂儿。
“这响动,不比秦淮河那些小调好听?”
朱高炽又抓起一块魷鱼丝塞嘴里,整个人透著股守財奴的亢奋。
“给你们交个实底。”
“听好了,別嚇得直接掉海里。”
“金子,纯度最高的,一百二十万两。”
“白银,按照大堂哥要求的法子提炼的顶级料子……八千万两。”
“咣当!”
蓝斌手里的望远镜直接砸在甲板上。
这位在山口城面对万军衝锋都没皱眉的小將,眼珠子瞪得滚圆。
“多……多少?”
“八千万两白银?”
蓝斌挨了好大一记闷棍。
“世子,你这手……没抖?没多拨几个零?”
“咱们大明这一年的岁入统共才几个钱?”
“你这一船,带回咱们三十年的国库?”
朱高炽撇了撇嘴,一脸的这种“格局打开”的表情。
“土包子。”
“这还没算山口城码头那一座座铜山。”
“你们那是杀得爽了,我是抄家抄到手软。”
“足利义满那个老鬼,把扶桑积攒千年的財富都搂进自己怀里。”
“一把火烧御所有个屁用?金子在土底下,它烧不化啊!”
朱高炽哼唧两声。
“我带著大內义弘那个老瘸子,挨家挨户敲门。”
“我说,大明天军帮你们清叛党,这是公道。”
“帮你们名正言顺,这是大恩。”
“既然有恩有德,你们这些大名、地主,是不是得拿点钱,给天军兄弟们买两件御寒的冬衣?”
朱高炽笑得一脸憨厚。
但在蓝春眼里,这笑容比他老子蓝玉的刀还狠,还毒。
“谁敢不给?”
“不给就是藐视朝廷,那就是足利余孽。”
“蓝大將军,你那神机营的枪子儿,可不是摆设。”
蓝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虚汗。
他看向远处那一望无际、吃水极深的庞大船队。
九艘大宝船,三十多艘副舰。
每一根桅杆都绷到极限。
那是泼天財富的重量。
“世子,末將这心里……发虚。”
蓝春看著朱高炽,语调都变了。
“以前我觉得,刀快就能打天下。”
“现在看这舱底,这世道,变了样。”
朱高炽咽下魷鱼丝。
他拍了拍那身松垮的袍子,目光看向遥远的北方。
那是大明金陵。
“大堂哥说过,这世上的道理,一半在炮管子里,另一半……就在这白银的成色里。”
“这一亿两,就是大明的骨头。”
朱高炽费劲地弯腰。
“我是想看看大堂哥的脸。”
“那人向来把一切摸得透透的,什么都算在前面。”
“这次,我要把这一亿两银子,一箱一箱地砸在他脚底下。”
“我得让他明白,打仗我確实不成;但论起搞钱,他得管我叫声祖宗!”
朱高炽越说越来劲,胖脸上的肉一顛一顛的。
他胸口堵著一股气。
在应天府被碾压智商,在船上吐一路丟脸面,全得在这一笔钱上挣回来。
这一亿两,就是他朱高炽挺起腰杆的本钱。
“蓝春,你说,要是咱们把银子拉进城,把御道都给铺平了,大堂哥会不会气得跳脚?”
蓝春尷尬地笑了笑,这问题他实在不敢接。
……
东海,大明海域。
原本翻涌的浊浪,撞上这支由钢铁巨舰组成的船队,也缓势头。
旗舰“镇海”號上。
瞭望员紧攥著黄铜望远镜,手心全是汗。
由於死盯海平线,他的眼眶早就烧得发红,但他不敢眨眼。
镜头里,那抹模糊的黛青色,正一点点变得清晰,变得稳固。
那不是雾,是陆地。
是那条被大明匠人修整过无数次的,代表家园的海岸线。
“陆地!!”
“看见陆地了!!”
“大明——!!我们回来啦!!”
尖叫声穿透海风,响彻甲板。
静止了。
镇海號上一下没了声响。
正准备换班的水手扔掉缆绳,顾不得手心的血泡,疯似的往船舷边冲。
正在舱底检查银球的甲士,不顾闷热,连滚带爬地顺著木梯往上钻。
万眾齐声吶喊。
“万胜——!!”
“大明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