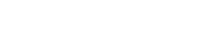2001年的农历年没有年三十。
腊月廿九过完,翻过夜就是大年初一。
高雪梅让秦道在腊月二十八上门吃饭。
时间选得很微妙。
既是在最临近过年的那两天,又避开了除夕当天的家庭核心时间。
像下棋时走的一步“试应手”,进可攻退可守。
第二天早上,秦道按时醒来。
窗外天光灰白,时间还早。
临近过年,村里反而安静。
没有农活要赶,没有急事要办,连狗叫都懒洋洋的。
他贪恋被子的温暖,难得没有立刻起床。
眼睛盯著天花板,看起来是发呆,实则是在思考。
他把今天中午可能遇到的情况在脑子里儘可能地预演一遍。
陆昭序的母亲叫他过去的目的,会问他什么问题……
直到九点半,窗外的阳光把屋里照得亮堂了些,他才起床。
简单吃了两碗玉米粥,又吃了几块买来过年的饼乾。
然后刷牙洗脸,穿上校服,背上背包。
走到父亲屋门口喊了一声:“爸,我中午不在家吃饭。”
正坐在木头沙发上看电视的秦发转过头,看了儿子一眼,点点头:“嗯”
他的眼睛里有种农民式的沉默——不是不懂,是不说。
然后转回头,继续看电视。
他知道儿子的社交范围,已经超出了他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的人的想像。
孩子要飞向天空,他帮不上忙,只能默默在看著,然后低头种地。
-----------------
秦道提前二十分钟到达工业局家属院。
他站在大院门口那两个大红灯笼下。
门卫室窗台上摆著几盆水仙,已经开了,小白花怯生生的。
然后他看见陆昭序从里面走出来。
她穿了件米白色的羽绒服,下身是深蓝色牛仔裤,脚上是双普通的运动鞋。
头髮扎成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
秦道迎了上去。
两人对视一眼。
“来了。”她说。
“嗯。”
陆昭序的眼睛比平日里要亮一些,甚至定定地盯著他看了两秒。
目光中,有一种她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亮光。
然后她这才转身:
“走吧。”
走进家属院,是另一个世界。
整齐的水泥路,两旁是六层的单元楼,阳台上晾著衣服、腊肉、香肠。
有小孩在空地上放鞭炮,“啪”一声脆响,然后咯咯笑。
陆昭序走在他侧前方半步。
快到单元门时,她忽然开口:
“我妈是八桂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是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扩散。”
“一个是研究產业经济,包括国內和国际。”
她顿了顿,像在背诵一份严谨的简介:
“她还是市科技顾问团成员,给政府提產业政策建议。”
说完,她转过头看了秦道一眼,补了一句:
“不过今天只是家宴,家里没別人,就我爸妈,放鬆点。”
这话听起来像安慰,但从她嘴里说出来,更像一份“情况通报”。
秦道点头:“明白。”
进入单元门,上楼。
墙上有孩子们用粉笔画的歪扭小人,还有各种“xxx是大笨蛋”的幼稚字跡。
到了三楼,陆昭序停下了脚步。
秦道看见右手边那扇深棕色的防盗门已经开了条缝。
门里透出暖黄的光,还有隱约的饭菜香。
然后门完全打开了。
秦道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站在门口。
一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质地柔软,里面是件烟粉色的高领毛衣,不张扬,但衬得人肤色温润。
下身是深蓝色的休閒裤,布料垂顺,脚上是一双浅灰色的软底家居鞋。
头髮梳得整齐,在脑后挽成简单的髮髻,一丝不乱。
鼻樑上架著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正看著他。
那目光很沉静,带著学者特有的平和。
秦道站在楼梯口,穿著校服,和一双洗得些发白的回力球鞋,背著黑色的背包。
楼道昏暗,他身后的窗户透进天光,给他轮廓镀了层毛边。
两人对视了大约三秒。
然后高雪梅嘴角微微弯起,眼角细纹舒展成一个温和的弧度。
“秦道吧?”她说,声音温和,“进来吧,外面冷。”
她侧身让开。
秦道点头:“高阿姨好。”
他没有立刻进门,而是打开背包,从包里取出一个米白色的棉布袋子。
他双手递过去:
“阿姨,这是家里自己晒的笋乾,今年冬笋好,给叔叔阿姨尝尝鲜——不是礼物,就是点土產。”
话说得朴素,但“尝尝鲜”三个字用得巧妙。
既表达了心意,又卸下了“上门送礼”的正式感,像邻居间隨手递一把自家种的青菜。
高雪梅明显顿了一下。
她目光在那布袋上停留了一瞬。
袋子上还有摺叠的痕跡,显然是精心准备,但包装朴素得恰到好处。
然后她伸手接过。
“谢谢。”她说,声音里多了份真实的温和,“你太客气了。”
她没有推辞,也没有说“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的客套话,只是很自然地把袋子接过去。
然后转身,在前面带路:“快进来吧。”
秦道这才迈步进门,然后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书。
整整一面墙的书柜,从地板顶到天花板,塞满了书。
不是装饰性的摆几本,是真正的、密密麻麻的、书脊挨著书脊的书墙。
书柜玻璃门擦得很乾净,但里面有些书显然经常被抽出来,书脊顏色比旁边的深。
书柜前是张老式写字檯,上面堆著文件、稿纸。
客厅不大,但整洁。
米白色的沙发,铺著素色沙发巾。
茶几上摆著果盘,里面有橙子,柚子,还有一些精致的点心。
沙发对面的柜子上,长虹电视正在静音播放午间新闻。
“坐。”高雪梅说,指了指沙发。
秦道把背包放在脚边,坐下。
陆昭序关上门,走进来,坐在他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高雪梅拿著东西去放到厨房,顺便倒了杯水,放在秦道面前的茶几上,杯底还沉著两片柠檬。
“阿书的爸爸正在做饭,”她说,也在对面沙发坐下,“我们先聊会儿。”
秦道瞥了一眼厨房,陆处长的身影正在忙碌。
空气中飘著饭菜香:莲藕燉排骨的醇厚,白切鸡的鲜甜,还有炒青菜的清爽……
八桂男儿,厨艺一绝。
最后的倔强,就是饭后不洗碗——不知道陆处长有没有保留八桂男儿最后的那份尊严。
高雪梅看著秦道,目光温和,但秦道能感觉到——那温和下面,是学者特有的锐利观察力。
窗外的腊月阳光斜斜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了光斑。
高雪梅端起紫砂杯,没喝,只是捧著,让掌心感受茶温。
动作有种学者特有的从容,像上课前整理讲义的教授。
“秦道,”她声音平和,“首先得谢谢你。”
“变频器那件事,你帮了阿书爸爸不小的忙,说句老实话,工业局那阵子压力很大。”
她顿了顿,目光透过镜片看向秦道:
“再加上这段时间,在家里时常听到你的名字。”
“阿书提,她爸爸也提。所以我就冒昧请你来吃顿饭,一来是感谢。”
“二来……”
腊月廿九过完,翻过夜就是大年初一。
高雪梅让秦道在腊月二十八上门吃饭。
时间选得很微妙。
既是在最临近过年的那两天,又避开了除夕当天的家庭核心时间。
像下棋时走的一步“试应手”,进可攻退可守。
第二天早上,秦道按时醒来。
窗外天光灰白,时间还早。
临近过年,村里反而安静。
没有农活要赶,没有急事要办,连狗叫都懒洋洋的。
他贪恋被子的温暖,难得没有立刻起床。
眼睛盯著天花板,看起来是发呆,实则是在思考。
他把今天中午可能遇到的情况在脑子里儘可能地预演一遍。
陆昭序的母亲叫他过去的目的,会问他什么问题……
直到九点半,窗外的阳光把屋里照得亮堂了些,他才起床。
简单吃了两碗玉米粥,又吃了几块买来过年的饼乾。
然后刷牙洗脸,穿上校服,背上背包。
走到父亲屋门口喊了一声:“爸,我中午不在家吃饭。”
正坐在木头沙发上看电视的秦发转过头,看了儿子一眼,点点头:“嗯”
他的眼睛里有种农民式的沉默——不是不懂,是不说。
然后转回头,继续看电视。
他知道儿子的社交范围,已经超出了他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的人的想像。
孩子要飞向天空,他帮不上忙,只能默默在看著,然后低头种地。
-----------------
秦道提前二十分钟到达工业局家属院。
他站在大院门口那两个大红灯笼下。
门卫室窗台上摆著几盆水仙,已经开了,小白花怯生生的。
然后他看见陆昭序从里面走出来。
她穿了件米白色的羽绒服,下身是深蓝色牛仔裤,脚上是双普通的运动鞋。
头髮扎成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
秦道迎了上去。
两人对视一眼。
“来了。”她说。
“嗯。”
陆昭序的眼睛比平日里要亮一些,甚至定定地盯著他看了两秒。
目光中,有一种她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亮光。
然后她这才转身:
“走吧。”
走进家属院,是另一个世界。
整齐的水泥路,两旁是六层的单元楼,阳台上晾著衣服、腊肉、香肠。
有小孩在空地上放鞭炮,“啪”一声脆响,然后咯咯笑。
陆昭序走在他侧前方半步。
快到单元门时,她忽然开口:
“我妈是八桂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是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扩散。”
“一个是研究產业经济,包括国內和国际。”
她顿了顿,像在背诵一份严谨的简介:
“她还是市科技顾问团成员,给政府提產业政策建议。”
说完,她转过头看了秦道一眼,补了一句:
“不过今天只是家宴,家里没別人,就我爸妈,放鬆点。”
这话听起来像安慰,但从她嘴里说出来,更像一份“情况通报”。
秦道点头:“明白。”
进入单元门,上楼。
墙上有孩子们用粉笔画的歪扭小人,还有各种“xxx是大笨蛋”的幼稚字跡。
到了三楼,陆昭序停下了脚步。
秦道看见右手边那扇深棕色的防盗门已经开了条缝。
门里透出暖黄的光,还有隱约的饭菜香。
然后门完全打开了。
秦道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站在门口。
一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质地柔软,里面是件烟粉色的高领毛衣,不张扬,但衬得人肤色温润。
下身是深蓝色的休閒裤,布料垂顺,脚上是一双浅灰色的软底家居鞋。
头髮梳得整齐,在脑后挽成简单的髮髻,一丝不乱。
鼻樑上架著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正看著他。
那目光很沉静,带著学者特有的平和。
秦道站在楼梯口,穿著校服,和一双洗得些发白的回力球鞋,背著黑色的背包。
楼道昏暗,他身后的窗户透进天光,给他轮廓镀了层毛边。
两人对视了大约三秒。
然后高雪梅嘴角微微弯起,眼角细纹舒展成一个温和的弧度。
“秦道吧?”她说,声音温和,“进来吧,外面冷。”
她侧身让开。
秦道点头:“高阿姨好。”
他没有立刻进门,而是打开背包,从包里取出一个米白色的棉布袋子。
他双手递过去:
“阿姨,这是家里自己晒的笋乾,今年冬笋好,给叔叔阿姨尝尝鲜——不是礼物,就是点土產。”
话说得朴素,但“尝尝鲜”三个字用得巧妙。
既表达了心意,又卸下了“上门送礼”的正式感,像邻居间隨手递一把自家种的青菜。
高雪梅明显顿了一下。
她目光在那布袋上停留了一瞬。
袋子上还有摺叠的痕跡,显然是精心准备,但包装朴素得恰到好处。
然后她伸手接过。
“谢谢。”她说,声音里多了份真实的温和,“你太客气了。”
她没有推辞,也没有说“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的客套话,只是很自然地把袋子接过去。
然后转身,在前面带路:“快进来吧。”
秦道这才迈步进门,然后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书。
整整一面墙的书柜,从地板顶到天花板,塞满了书。
不是装饰性的摆几本,是真正的、密密麻麻的、书脊挨著书脊的书墙。
书柜玻璃门擦得很乾净,但里面有些书显然经常被抽出来,书脊顏色比旁边的深。
书柜前是张老式写字檯,上面堆著文件、稿纸。
客厅不大,但整洁。
米白色的沙发,铺著素色沙发巾。
茶几上摆著果盘,里面有橙子,柚子,还有一些精致的点心。
沙发对面的柜子上,长虹电视正在静音播放午间新闻。
“坐。”高雪梅说,指了指沙发。
秦道把背包放在脚边,坐下。
陆昭序关上门,走进来,坐在他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高雪梅拿著东西去放到厨房,顺便倒了杯水,放在秦道面前的茶几上,杯底还沉著两片柠檬。
“阿书的爸爸正在做饭,”她说,也在对面沙发坐下,“我们先聊会儿。”
秦道瞥了一眼厨房,陆处长的身影正在忙碌。
空气中飘著饭菜香:莲藕燉排骨的醇厚,白切鸡的鲜甜,还有炒青菜的清爽……
八桂男儿,厨艺一绝。
最后的倔强,就是饭后不洗碗——不知道陆处长有没有保留八桂男儿最后的那份尊严。
高雪梅看著秦道,目光温和,但秦道能感觉到——那温和下面,是学者特有的锐利观察力。
窗外的腊月阳光斜斜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了光斑。
高雪梅端起紫砂杯,没喝,只是捧著,让掌心感受茶温。
动作有种学者特有的从容,像上课前整理讲义的教授。
“秦道,”她声音平和,“首先得谢谢你。”
“变频器那件事,你帮了阿书爸爸不小的忙,说句老实话,工业局那阵子压力很大。”
她顿了顿,目光透过镜片看向秦道:
“再加上这段时间,在家里时常听到你的名字。”
“阿书提,她爸爸也提。所以我就冒昧请你来吃顿饭,一来是感谢。”
“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