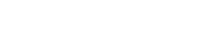一大清早,周正清已经带著他的小队伍出发了。
他依旧穿著那件万民衣,头上戴著当地常见的竹笠。
他手里拿著的,不仅是简单的红薯种和盐巴口袋,还有连夜赶製出来的禁毒安民告示,以及一份根据陛下的严令,由他细化的劝导戒断、以工代賑初步章程。
昨夜接到陛下那道杀气腾腾的諭令后。
他浑身热血沸腾,恨不能大半夜就去实施陛下命令,可惜天黑路滑,被番子给阻止了。
周正清躺在床上一夜未眠,反覆推敲,细细思索著如何既能震慑不法,又不至嚇坏那些可能被胁迫或懵懂无知的普通山民。
“王五叔,”
周正清对一位年纪稍长的嚮导说,
“今日我们去的水洼寨,头人昨日態度还算恭顺,但似乎有些隱瞒。到了寨子,你且按我昨日交代的,先与相熟的人家聊聊,听听寨子里关於黑泥或极乐膏的风声,尤其留意有没有人最近行为反常,或者家里突然宽裕又说不出来路的。”
王五叔用力点头:
“周大人放心,水洼寨我有个远房表亲,是个老实猎户,嘴巴严,我去问他。”
队伍沉默地穿行在林间小径上。
周正清的心思却已飞到寨中。
陛下將如此重任託付,他深感压力,却也斗志昂扬。
这禁毒之事,比在西北救灾更复杂,因涉及人心痼疾与暴利诱惑。
但他相信,只要如英明的陛下所示,恩威並施,一面以雷霆手段斩断毒源,一面以实在活路引导百姓,总能水滴石穿。
......
......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支队伍从一號驛不同的方向悄无声息地没入山林。
这支队伍人数更少,仅八人,皆著便於隱匿的与周围景色一致的劲装,行动间几乎与丛林融为一体。
为首的是正是鼻子灵的邪门的冯档头,他此刻手中拿著一张简陋的草图。
向著推断出的可能製贩极乐膏窝点的大致地方探查去。
冯档头一边领路一边鼻翼几不可察地翕动著。
“档头,这都绕了三道坡了,连个鬼影子都没……”
一个年轻些的番子压低声音,话没说完,就被冯档头抬手止住。
冯档头没回头,只是侧著脸,鼻翼微微动了两下。
他伸出两根手指,指了指左前方一片看起来毫无异常的崖壁下方。
“那边,三十丈,有灶火气,还有一股熬过头了的糖精味儿。”
几个番子面面相覷,虽然早知道自家档头本事,每次亲耳听见还是觉得有点玄乎。
但他们毫不迟疑,立刻按照冯档头无声的手势散开,两人悄无声息地向上风头摸去查探,其余人则跟著冯档头,借著林木阴影,向那处崖壁潜行。
越靠近,那股子混合的气味就越明显。
连几个鼻子普通的番子也能隱约闻到一丝甜腻腻、让人有点头晕的味道。
就是这里了。
几个番子无声地调整著位置与姿態,封死了前方草棚区域所有可能逃遁的路径。
冯档头没有急於下令突击。
他需要再確认一些细节,来確保这个草棚確实是真正的製毒作坊。
借著林隙透下的微光,冯档头目光仔细扫视著那两座草棚。
棚子搭得潦草,但位置选得刁钻,背靠陡坡,前临溪流,两侧林木相对稀疏,视野却受高地灌木所限,极其隱秘,並且易守难攻。
他又悄悄远远对著棚子绕了一圈。
这个棚子只有一个门口,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他回到原地。
棚外那三个守卫状態,印证了他的部分猜测。
离他最近的那个,背靠著一棵乾枯的树干,脑袋一点一点地打著瞌睡。
即使隔著二十几步,冯档头也能看到那人眼下一片乌青,脸颊瘦削地凹陷下去,裸露的脖颈和手背上,有几处已经结痂的溃烂痕跡。
另外两个更是如此,脚步虚浮,眼神无法长时间聚焦,时不时贪婪地呼吸著空气中那奇怪的气味。
这守卫如同废人,癮已深,神智半失,根本不足为虑。
看来就是这里了!
冯档头心中判断。
他的目光投向草棚缝隙。
隱约能看到里面有人影晃动,还有低低的交谈声,伴隨著瓦罐轻碰的叮噹声。
气味也更浓烈地从那里散发出来。
是时候了!
冯档头从腰间革囊(防水的皮囊)里摸出两枚特製的蜡丸,然后捏碎。
一股异常醒脑的薄荷混合著辛辣药草的气息弥散开来,被他和他身后的手下们吸入。
这是东厂用於对抗迷烟或秽气的简易药散,也能提神。
他最后检查了一遍袖箭和淬毒短刃,然后,右手前猛地一挥!
就在准备动手的剎那,冯档头鼻翼又急促地抽动了两下,脸色一变,猛地挥手制止了即將扑出的手下。
“等等!”
他声音压得极低,
“情况不对,棚子里有新的血腥味!”
他话音刚落,溪边草棚里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惨叫,隨即是重物倒地的闷响和一阵慌乱的碰撞声。
棚外三个守卫惊得跳起来。
“內訌?还是灭口?”
冯档头心念电转。
他当机立断,手势一变。
强攻!
“咻咻咻——!”
几乎在他手势落下的瞬间,三支从不同角度射出的弩箭,精准无比地钉在了三个守卫脚前不到一寸的地面上!
箭矢入土,箭尾剧颤,发出令人心悸的嗡鸣。
三个守卫茫然四顾,脸上血色瞬间褪去,瘫坐在地上。
“玄秦东厂!跪地者生!”
几个冰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说著標准的南疆话。
三个守卫这才骇然发现,不知何时,几个如同鬼魅般的番子,已经呈扇形將他们和草棚围住,手里持著劲弩指著他们,眼里闪著寒光。
“饶命!饶命啊官爷!”
原本靠在树上的那个最先崩溃,丟掉手里的破刀,噗通跪倒,连连磕头。
另外两个也魂飞魄散,慌忙扔了武器,跪倒在地,浑身筛糠。
冯档头没有看他们,身形一晃,带著两个人早已掠到草棚入口旁!
他依旧穿著那件万民衣,头上戴著当地常见的竹笠。
他手里拿著的,不仅是简单的红薯种和盐巴口袋,还有连夜赶製出来的禁毒安民告示,以及一份根据陛下的严令,由他细化的劝导戒断、以工代賑初步章程。
昨夜接到陛下那道杀气腾腾的諭令后。
他浑身热血沸腾,恨不能大半夜就去实施陛下命令,可惜天黑路滑,被番子给阻止了。
周正清躺在床上一夜未眠,反覆推敲,细细思索著如何既能震慑不法,又不至嚇坏那些可能被胁迫或懵懂无知的普通山民。
“王五叔,”
周正清对一位年纪稍长的嚮导说,
“今日我们去的水洼寨,头人昨日態度还算恭顺,但似乎有些隱瞒。到了寨子,你且按我昨日交代的,先与相熟的人家聊聊,听听寨子里关於黑泥或极乐膏的风声,尤其留意有没有人最近行为反常,或者家里突然宽裕又说不出来路的。”
王五叔用力点头:
“周大人放心,水洼寨我有个远房表亲,是个老实猎户,嘴巴严,我去问他。”
队伍沉默地穿行在林间小径上。
周正清的心思却已飞到寨中。
陛下將如此重任託付,他深感压力,却也斗志昂扬。
这禁毒之事,比在西北救灾更复杂,因涉及人心痼疾与暴利诱惑。
但他相信,只要如英明的陛下所示,恩威並施,一面以雷霆手段斩断毒源,一面以实在活路引导百姓,总能水滴石穿。
......
......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支队伍从一號驛不同的方向悄无声息地没入山林。
这支队伍人数更少,仅八人,皆著便於隱匿的与周围景色一致的劲装,行动间几乎与丛林融为一体。
为首的是正是鼻子灵的邪门的冯档头,他此刻手中拿著一张简陋的草图。
向著推断出的可能製贩极乐膏窝点的大致地方探查去。
冯档头一边领路一边鼻翼几不可察地翕动著。
“档头,这都绕了三道坡了,连个鬼影子都没……”
一个年轻些的番子压低声音,话没说完,就被冯档头抬手止住。
冯档头没回头,只是侧著脸,鼻翼微微动了两下。
他伸出两根手指,指了指左前方一片看起来毫无异常的崖壁下方。
“那边,三十丈,有灶火气,还有一股熬过头了的糖精味儿。”
几个番子面面相覷,虽然早知道自家档头本事,每次亲耳听见还是觉得有点玄乎。
但他们毫不迟疑,立刻按照冯档头无声的手势散开,两人悄无声息地向上风头摸去查探,其余人则跟著冯档头,借著林木阴影,向那处崖壁潜行。
越靠近,那股子混合的气味就越明显。
连几个鼻子普通的番子也能隱约闻到一丝甜腻腻、让人有点头晕的味道。
就是这里了。
几个番子无声地调整著位置与姿態,封死了前方草棚区域所有可能逃遁的路径。
冯档头没有急於下令突击。
他需要再確认一些细节,来確保这个草棚確实是真正的製毒作坊。
借著林隙透下的微光,冯档头目光仔细扫视著那两座草棚。
棚子搭得潦草,但位置选得刁钻,背靠陡坡,前临溪流,两侧林木相对稀疏,视野却受高地灌木所限,极其隱秘,並且易守难攻。
他又悄悄远远对著棚子绕了一圈。
这个棚子只有一个门口,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他回到原地。
棚外那三个守卫状態,印证了他的部分猜测。
离他最近的那个,背靠著一棵乾枯的树干,脑袋一点一点地打著瞌睡。
即使隔著二十几步,冯档头也能看到那人眼下一片乌青,脸颊瘦削地凹陷下去,裸露的脖颈和手背上,有几处已经结痂的溃烂痕跡。
另外两个更是如此,脚步虚浮,眼神无法长时间聚焦,时不时贪婪地呼吸著空气中那奇怪的气味。
这守卫如同废人,癮已深,神智半失,根本不足为虑。
看来就是这里了!
冯档头心中判断。
他的目光投向草棚缝隙。
隱约能看到里面有人影晃动,还有低低的交谈声,伴隨著瓦罐轻碰的叮噹声。
气味也更浓烈地从那里散发出来。
是时候了!
冯档头从腰间革囊(防水的皮囊)里摸出两枚特製的蜡丸,然后捏碎。
一股异常醒脑的薄荷混合著辛辣药草的气息弥散开来,被他和他身后的手下们吸入。
这是东厂用於对抗迷烟或秽气的简易药散,也能提神。
他最后检查了一遍袖箭和淬毒短刃,然后,右手前猛地一挥!
就在准备动手的剎那,冯档头鼻翼又急促地抽动了两下,脸色一变,猛地挥手制止了即將扑出的手下。
“等等!”
他声音压得极低,
“情况不对,棚子里有新的血腥味!”
他话音刚落,溪边草棚里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惨叫,隨即是重物倒地的闷响和一阵慌乱的碰撞声。
棚外三个守卫惊得跳起来。
“內訌?还是灭口?”
冯档头心念电转。
他当机立断,手势一变。
强攻!
“咻咻咻——!”
几乎在他手势落下的瞬间,三支从不同角度射出的弩箭,精准无比地钉在了三个守卫脚前不到一寸的地面上!
箭矢入土,箭尾剧颤,发出令人心悸的嗡鸣。
三个守卫茫然四顾,脸上血色瞬间褪去,瘫坐在地上。
“玄秦东厂!跪地者生!”
几个冰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说著標准的南疆话。
三个守卫这才骇然发现,不知何时,几个如同鬼魅般的番子,已经呈扇形將他们和草棚围住,手里持著劲弩指著他们,眼里闪著寒光。
“饶命!饶命啊官爷!”
原本靠在树上的那个最先崩溃,丟掉手里的破刀,噗通跪倒,连连磕头。
另外两个也魂飞魄散,慌忙扔了武器,跪倒在地,浑身筛糠。
冯档头没有看他们,身形一晃,带著两个人早已掠到草棚入口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