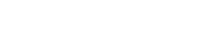郑文渊皱了皱眉,手指在那朴拙的字跡上敲了敲,像在敲什么不入流的东西:
“字体差了些,文章不够华美,用典也少。尤其这治水一段,满篇泥沙石料,几近匠人之言,失了文气。”
他顿了顿,继续补充道:
“科举取士,取的是治国之才,不是工匠之流。文章若失了风骨,纵有千般实务,终是下乘,尤其是字如其人,字不好这人也就不怎么行!”
话音落下,旁边几位清流派考官纷纷附和。
“郑大人所言极是,字如其人啊!”
“文以载道,辞藻亦是大道。”
“此子文采,確实平平。”
小顺子静静地听著,脸上笑容不变,心里默默地给开口的几人判了死刑。
等他们说完了,小顺子柔声问道:
“那依各位大人看,这份卷子,该评几等?”
郑文渊与左右交换了眼色,缓缓道:
“丙等中。”
丙等中。
二十名里,排十五六位。
不上不下,勉强中游。
但今科寒门考生本就少,这个排名,等於落榜。
小顺子“哦”了一声,没再问。
......
......
第二天一早,陈实是被巷子里的喧譁声吵醒的。
他睁开眼,天刚蒙蒙亮。
外头传来村头大妈的议论声:
“听说了吗?阅卷出事了!”
“啥事?”
“东厂的人闯进阅卷房了!把那些考官全堵在里头!”
“真的假的?!”
“千真万確!我家二小子在礼部后街当杂役,亲眼看见的!那个魏公公,抱著个匣子进去的,好几个时辰没出来!”
陈实坐起身,心臟突突直跳。
东厂?
那个传说中专替皇帝干脏活的东厂?
他们去阅卷房干什么?
陈实连忙穿好衣服,推门出去。
巷子里已经聚了好几个人,都是附近的街坊,一个个脸上写满了我有內幕消息。
“要我说,早该管管了!”
卖豆腐的老王头啐了一口,“那些考官,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咱们这样的,写得再好也入不了他们的眼!”
“可东厂插手……这不合规矩吧?”旁边有人小声嘀咕。
“规矩?”
老王头冷笑,“规矩是他们定的,他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现在好了,陛下派人来改规矩了!”
陈实站在门口,听著这些话,脑子里乱糟糟的。
东厂插手阅卷,是为了寒门考生?
可能吗?
那个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魏公公,会替他们这些泥腿子出头?
他心里涌起一丝渺茫的希望,可很快又被压了下去。
不可能的。
这么多年了,从爷爷那辈起,寒门子弟想要出头,就得给世家当狗,就得学会写那些自己都不信的花团锦簇的文章,就得把良心和骨头都磨碎了,咽下去。
陛下?
陛下离他们太远了。
远得像天上的云,看得见,摸不著。
“陈实!”
巷子口传来喊声。
是前街的韩江,也是今科考生,家里开豆腐坊的,勉强算个寒门。
他跑得气喘吁吁,脸上又是汗又是灰:
“你听说了吗?阅卷房出事了!”
陈实点点头:“刚听说。”
“我爹托人打听了!”
韩江压低声音,眼睛发亮,“说东厂那个魏公公,抱著一匣子帐本进去的!把那些考官的老底全掀了!现在里头正改卷子呢!”
帐本?
陈实心里一紧。
“什么帐本?”
“还能是什么?”
韩江咧嘴一笑,“贪赃枉法、强占民田、纵奴行凶的帐本唄,一个个看著人模狗样,结果......”
他说得兴奋,唾沫星子乱飞:
“这下好了!有这些把柄捏著,看他们还敢不敢压咱们的卷子!”
陈实没说话。
他想起自己那份朴拙的考卷,想起那些没有半点文采的句子。
就算考官不敢压卷子了,可他的文章,真的能入那些“大儒”的眼吗?
“韩江。”
他突然开口,“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韩江愣了愣,隨即挠挠头:“就那样吧。我爹说了,咱们这样的人家,別想什么花团锦簇,能把事儿说明白就行。我写的是商税——我家做豆腐,这些年被税卡扒了多少层皮,我全写进去了。”
他说著,眼睛又亮起来:
“陈实,你说……这次会不会真的不一样?”
陈实看著他那张充满希望的脸,想起父亲昨晚的话,想起张婶的传言,想起这些年见过的、听过的所有寒门学子的结局。
最后,他只是拍了拍韩江的肩膀。
“等放榜吧。”
等。
这个字,像块石头,压在陈实心口。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阅卷房那边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一会儿说东厂还在里头,一会儿说已经有考官扛不住晕过去了,一会儿又说榜单快要定了。
巷子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每天都有考生家人聚在一起,交换著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
有人说这次寒门要大胜,有人说世家反扑了,有人说陛下震怒了要彻查。
陈实没去凑热闹。
他每天早早起床,把家里那点粟米数一遍,把水缸挑满,把塌了的院墙再加固加固。
然后搬个小凳坐在门口,手里拿著本玄秦图书馆借来的圣皇陛下的起居录翻阅著。
父亲陈老根咳嗽得更厉害了。
咳得厉害的时候,像要把五臟六腑都咳出来。
陈实去请郎中,郎中说要用人参吊著,可一根人参的价钱,够他们父子吃半年粟米。
他拿不出来。
只能每天去山上挖些草药,熬了给父亲喝。
药很苦,父亲喝的时候眉头皱得死紧,可喝完了,总会拍拍他的手:
“没事,爹命硬。”
穷人家的人都命硬。
陈实低著头,不敢看父亲的眼睛。
他知道,爹在等。
等一个可能永远等不来的好消息。
等一个能改变他们这个家、这条巷子、甚至所有寒门子弟命运的消息。
第三天傍晚,陈实正在灶台边熬药,巷子里突然炸开了锅。
他手一抖,药罐子差点打翻。
外头传来哭嚎声、骂声,还有东西砸在地上的破碎声。
出什么事了?!
他放下药罐,连忙推门出去。
“字体差了些,文章不够华美,用典也少。尤其这治水一段,满篇泥沙石料,几近匠人之言,失了文气。”
他顿了顿,继续补充道:
“科举取士,取的是治国之才,不是工匠之流。文章若失了风骨,纵有千般实务,终是下乘,尤其是字如其人,字不好这人也就不怎么行!”
话音落下,旁边几位清流派考官纷纷附和。
“郑大人所言极是,字如其人啊!”
“文以载道,辞藻亦是大道。”
“此子文采,確实平平。”
小顺子静静地听著,脸上笑容不变,心里默默地给开口的几人判了死刑。
等他们说完了,小顺子柔声问道:
“那依各位大人看,这份卷子,该评几等?”
郑文渊与左右交换了眼色,缓缓道:
“丙等中。”
丙等中。
二十名里,排十五六位。
不上不下,勉强中游。
但今科寒门考生本就少,这个排名,等於落榜。
小顺子“哦”了一声,没再问。
......
......
第二天一早,陈实是被巷子里的喧譁声吵醒的。
他睁开眼,天刚蒙蒙亮。
外头传来村头大妈的议论声:
“听说了吗?阅卷出事了!”
“啥事?”
“东厂的人闯进阅卷房了!把那些考官全堵在里头!”
“真的假的?!”
“千真万確!我家二小子在礼部后街当杂役,亲眼看见的!那个魏公公,抱著个匣子进去的,好几个时辰没出来!”
陈实坐起身,心臟突突直跳。
东厂?
那个传说中专替皇帝干脏活的东厂?
他们去阅卷房干什么?
陈实连忙穿好衣服,推门出去。
巷子里已经聚了好几个人,都是附近的街坊,一个个脸上写满了我有內幕消息。
“要我说,早该管管了!”
卖豆腐的老王头啐了一口,“那些考官,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咱们这样的,写得再好也入不了他们的眼!”
“可东厂插手……这不合规矩吧?”旁边有人小声嘀咕。
“规矩?”
老王头冷笑,“规矩是他们定的,他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现在好了,陛下派人来改规矩了!”
陈实站在门口,听著这些话,脑子里乱糟糟的。
东厂插手阅卷,是为了寒门考生?
可能吗?
那个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魏公公,会替他们这些泥腿子出头?
他心里涌起一丝渺茫的希望,可很快又被压了下去。
不可能的。
这么多年了,从爷爷那辈起,寒门子弟想要出头,就得给世家当狗,就得学会写那些自己都不信的花团锦簇的文章,就得把良心和骨头都磨碎了,咽下去。
陛下?
陛下离他们太远了。
远得像天上的云,看得见,摸不著。
“陈实!”
巷子口传来喊声。
是前街的韩江,也是今科考生,家里开豆腐坊的,勉强算个寒门。
他跑得气喘吁吁,脸上又是汗又是灰:
“你听说了吗?阅卷房出事了!”
陈实点点头:“刚听说。”
“我爹托人打听了!”
韩江压低声音,眼睛发亮,“说东厂那个魏公公,抱著一匣子帐本进去的!把那些考官的老底全掀了!现在里头正改卷子呢!”
帐本?
陈实心里一紧。
“什么帐本?”
“还能是什么?”
韩江咧嘴一笑,“贪赃枉法、强占民田、纵奴行凶的帐本唄,一个个看著人模狗样,结果......”
他说得兴奋,唾沫星子乱飞:
“这下好了!有这些把柄捏著,看他们还敢不敢压咱们的卷子!”
陈实没说话。
他想起自己那份朴拙的考卷,想起那些没有半点文采的句子。
就算考官不敢压卷子了,可他的文章,真的能入那些“大儒”的眼吗?
“韩江。”
他突然开口,“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韩江愣了愣,隨即挠挠头:“就那样吧。我爹说了,咱们这样的人家,別想什么花团锦簇,能把事儿说明白就行。我写的是商税——我家做豆腐,这些年被税卡扒了多少层皮,我全写进去了。”
他说著,眼睛又亮起来:
“陈实,你说……这次会不会真的不一样?”
陈实看著他那张充满希望的脸,想起父亲昨晚的话,想起张婶的传言,想起这些年见过的、听过的所有寒门学子的结局。
最后,他只是拍了拍韩江的肩膀。
“等放榜吧。”
等。
这个字,像块石头,压在陈实心口。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阅卷房那边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一会儿说东厂还在里头,一会儿说已经有考官扛不住晕过去了,一会儿又说榜单快要定了。
巷子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每天都有考生家人聚在一起,交换著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
有人说这次寒门要大胜,有人说世家反扑了,有人说陛下震怒了要彻查。
陈实没去凑热闹。
他每天早早起床,把家里那点粟米数一遍,把水缸挑满,把塌了的院墙再加固加固。
然后搬个小凳坐在门口,手里拿著本玄秦图书馆借来的圣皇陛下的起居录翻阅著。
父亲陈老根咳嗽得更厉害了。
咳得厉害的时候,像要把五臟六腑都咳出来。
陈实去请郎中,郎中说要用人参吊著,可一根人参的价钱,够他们父子吃半年粟米。
他拿不出来。
只能每天去山上挖些草药,熬了给父亲喝。
药很苦,父亲喝的时候眉头皱得死紧,可喝完了,总会拍拍他的手:
“没事,爹命硬。”
穷人家的人都命硬。
陈实低著头,不敢看父亲的眼睛。
他知道,爹在等。
等一个可能永远等不来的好消息。
等一个能改变他们这个家、这条巷子、甚至所有寒门子弟命运的消息。
第三天傍晚,陈实正在灶台边熬药,巷子里突然炸开了锅。
他手一抖,药罐子差点打翻。
外头传来哭嚎声、骂声,还有东西砸在地上的破碎声。
出什么事了?!
他放下药罐,连忙推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