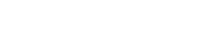第195章 其罪
“饶过他们了。”
张汤犹有不甘道。
依大汉律,造反者诛三族。
真正的诛族之景,可不是所谓的一个个直接斩首,而是要分六步。
第一步,“黥”,在脸上刺字,表明这是犯人。
第二步,“劓”,把鼻子削掉。
第三步,“斩”,斩掉手、脚各十指。
第四步,“笞”,用竹板将之活活打死。
第五步,“枭”,将死尸头颅砍下。
第六步,“菹”,剐下无头死尸的肉,制成肉酱。
这才是大汉造反之罪的刑罚,在此之前,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便是如此之诛。
也因此逼反了九江王英布。
从高皇帝立国至今,大汉“复辟”大罪仅此一例,具体刑罚只能参考秦朝。
在“造反”、“复辟”两项大罪刑罚之间,张汤思虑了许久,最终选择了复辟刑罚。
与枭首制肉酱相比,坑杀显得那么仁慈,此时此刻的张汤,竟有种“善人”的自我感觉。
边通遍体生寒。
不知道为何,他总觉得现在的大汉朝廷,是群狼在堂,而他,身居高位却如一只土犬,登堂入室时,恍惚犬在狼群,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中外两朝公卿、将军、列侯、宗室大臣里面,到底还有多少人是这种杀了别人全族,还要让别人说谢谢的恐怖存在?
“悉听大司空吩咐。”边通选择了听命行事。
……
入秋时节,渭水草滩再次被选作刑场,人海汪洋不息。
秋月刑杀,这是华夏最古老的传统之一。
《吕氏春秋》云:“孟秋之月,以立秋……是月也,修法制,决狱讼,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盈。”
这般天人交相应的政事规矩,在眼下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谁也不会惊讶,但这次,关中人众所以惊讶骚动而络绎赶来者,对“要杀之众”而不可思议也。
精明的商人乘机摆起了各种小摊,专门向观刑者卖水卖茶卖酒卖饭卖零碎杂物,草滩之上,生意又一次为之兴隆。
大汉刑杀向来不禁观者,观刑人众从渭水两岸一直铺满到刑场四周,却静悄悄地再没了气息。
人们惊奇地发现,今日这个刑场大是怪异,没有刑架木桩,也没有赤膊红衣的刽子手。
划定的刑场内,只有数以千计的吏卒在掘坑,一排排大土坑相连,从地下翻出的新鲜泥土气息,不知为何,看得人心砰砰直跳。
观刑的关中百姓三三两两低声交谈着,似是在说朝廷心善,要杀了人犯后就地埋葬,不至于连葬身之地都没有。
奉诏令观刑的中外两朝公卿大夫、列侯亲贵、宗室大臣却都紧咬着牙关不说话,脸色苍白。
庶民匹夫不知道的事,他们有着很多方法可以打探,可以提前知晓,就比如今日刑杀的手段。
天日烈烈,在这流火之月,热的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的,如果不是徐徐河风吹着,人怕是站在那里都熬不住。
行刑的时刻是天定的,午时一到,刑场中央的土台上,两排号角立刻齐名,数以万计的人犯百人一队,来到了挖掘好的大土坑前。
这时,任谁都觉察出了异样,观刑的关中百姓,话说着说着就不说了。
“主刑大臣到!”
随着司刑大将的声音,御史大夫张汤、廷尉卿边通缓缓走上监刑台。
这是块用新土堆成的高台,边通受命,宣读了决刑书。
“大汉皇太子诏:查左冯翊义纵、强弩将军李沮携私卫部曲三千二百一十六人,不思朝廷善待之恩,散布妖言,毁谤皇帝,非议当国储君,勾连内外不臣者,闯京逼宫,图谋造反,屡犯法令,罪不容诛!
为绝以武乱禁之恶风,为绝造反阴谋之得逞,将所有触犯律法之犯连同三族处坑杀之刑!
元狩二年季夏。”
诏毕。
张汤立时上前,高喝道:“鸣鼓!行刑!”
从昼到夜,所有的观刑者都没有离去,也永远不会忘记今时今日。
多年以后,草滩早就长出了新草,恢复了原样,但两朝官吏和关中百姓始终记得这样一个午后。
无数人被推下深深的土坑,泥土逐渐飞扬起来,那连成片的凄厉惨叫,在一铲铲黄土覆盖后,渐渐沉闷,渐渐地没有了声息。
两个时辰后,掩埋的土坑再次被挖开,行刑吏卒开始往里面灌注猛火油,张汤扔入了火把。
热易生疫,又紧邻滋养无数关中田地、百姓的渭河,不能留下任何危险。
一个个“火焰坑”冲天而起,行刑者、观刑者的面容都在火焰中扭曲,燃烧过后飘落的黑灰,落到人的身上,顿时便会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关中平原的夜空被照亮,直至黎明的到来,方才迟迟熄灭。
余烬未散的坑洞里,没了人的痕迹,只剩下未有完全化成灰的骨头,张汤检验过后,命令行刑吏卒掩埋。
监刑台也被拆掉,那些土全部填回了坑洞之中,刚刚好。
“从今往后,大司空你我,便是后世唾骂的‘狗官’了。”
边通踩着热土,为自己的身后名叹息。
上一个坑杀这么多人的还是秦朝武安君白起,长平一战,白起坑杀了赵国四十万降卒,为之不祥,被秦昭襄王赐死杜邮。
他莫名地觉得,自己的寿短了些。
也在担心死后,后人对主刑的自己如何评价,上君走狗?亦或是鹰犬。
正要上车架的张汤脚步一顿,回头望着他,“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我相信我之后,会有无数后人为我粉饰是非。”
作为一名纯粹的酷吏,他做了这么多事,在后世的声誉,哪怕再坏,也坏不过商鞅,他和商鞅,也会成为所有法吏的丰碑。
依然是那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言罢,张汤便上了车架,车轮辚辚驶向长安城。
“大司空,为何这么心急?”
边通望着车尾,十分不明白,只听车过之处,昂然的声音传来,“来不及了,我要去踹儒人的坟!”
(本章完)
“饶过他们了。”
张汤犹有不甘道。
依大汉律,造反者诛三族。
真正的诛族之景,可不是所谓的一个个直接斩首,而是要分六步。
第一步,“黥”,在脸上刺字,表明这是犯人。
第二步,“劓”,把鼻子削掉。
第三步,“斩”,斩掉手、脚各十指。
第四步,“笞”,用竹板将之活活打死。
第五步,“枭”,将死尸头颅砍下。
第六步,“菹”,剐下无头死尸的肉,制成肉酱。
这才是大汉造反之罪的刑罚,在此之前,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便是如此之诛。
也因此逼反了九江王英布。
从高皇帝立国至今,大汉“复辟”大罪仅此一例,具体刑罚只能参考秦朝。
在“造反”、“复辟”两项大罪刑罚之间,张汤思虑了许久,最终选择了复辟刑罚。
与枭首制肉酱相比,坑杀显得那么仁慈,此时此刻的张汤,竟有种“善人”的自我感觉。
边通遍体生寒。
不知道为何,他总觉得现在的大汉朝廷,是群狼在堂,而他,身居高位却如一只土犬,登堂入室时,恍惚犬在狼群,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中外两朝公卿、将军、列侯、宗室大臣里面,到底还有多少人是这种杀了别人全族,还要让别人说谢谢的恐怖存在?
“悉听大司空吩咐。”边通选择了听命行事。
……
入秋时节,渭水草滩再次被选作刑场,人海汪洋不息。
秋月刑杀,这是华夏最古老的传统之一。
《吕氏春秋》云:“孟秋之月,以立秋……是月也,修法制,决狱讼,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盈。”
这般天人交相应的政事规矩,在眼下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谁也不会惊讶,但这次,关中人众所以惊讶骚动而络绎赶来者,对“要杀之众”而不可思议也。
精明的商人乘机摆起了各种小摊,专门向观刑者卖水卖茶卖酒卖饭卖零碎杂物,草滩之上,生意又一次为之兴隆。
大汉刑杀向来不禁观者,观刑人众从渭水两岸一直铺满到刑场四周,却静悄悄地再没了气息。
人们惊奇地发现,今日这个刑场大是怪异,没有刑架木桩,也没有赤膊红衣的刽子手。
划定的刑场内,只有数以千计的吏卒在掘坑,一排排大土坑相连,从地下翻出的新鲜泥土气息,不知为何,看得人心砰砰直跳。
观刑的关中百姓三三两两低声交谈着,似是在说朝廷心善,要杀了人犯后就地埋葬,不至于连葬身之地都没有。
奉诏令观刑的中外两朝公卿大夫、列侯亲贵、宗室大臣却都紧咬着牙关不说话,脸色苍白。
庶民匹夫不知道的事,他们有着很多方法可以打探,可以提前知晓,就比如今日刑杀的手段。
天日烈烈,在这流火之月,热的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的,如果不是徐徐河风吹着,人怕是站在那里都熬不住。
行刑的时刻是天定的,午时一到,刑场中央的土台上,两排号角立刻齐名,数以万计的人犯百人一队,来到了挖掘好的大土坑前。
这时,任谁都觉察出了异样,观刑的关中百姓,话说着说着就不说了。
“主刑大臣到!”
随着司刑大将的声音,御史大夫张汤、廷尉卿边通缓缓走上监刑台。
这是块用新土堆成的高台,边通受命,宣读了决刑书。
“大汉皇太子诏:查左冯翊义纵、强弩将军李沮携私卫部曲三千二百一十六人,不思朝廷善待之恩,散布妖言,毁谤皇帝,非议当国储君,勾连内外不臣者,闯京逼宫,图谋造反,屡犯法令,罪不容诛!
为绝以武乱禁之恶风,为绝造反阴谋之得逞,将所有触犯律法之犯连同三族处坑杀之刑!
元狩二年季夏。”
诏毕。
张汤立时上前,高喝道:“鸣鼓!行刑!”
从昼到夜,所有的观刑者都没有离去,也永远不会忘记今时今日。
多年以后,草滩早就长出了新草,恢复了原样,但两朝官吏和关中百姓始终记得这样一个午后。
无数人被推下深深的土坑,泥土逐渐飞扬起来,那连成片的凄厉惨叫,在一铲铲黄土覆盖后,渐渐沉闷,渐渐地没有了声息。
两个时辰后,掩埋的土坑再次被挖开,行刑吏卒开始往里面灌注猛火油,张汤扔入了火把。
热易生疫,又紧邻滋养无数关中田地、百姓的渭河,不能留下任何危险。
一个个“火焰坑”冲天而起,行刑者、观刑者的面容都在火焰中扭曲,燃烧过后飘落的黑灰,落到人的身上,顿时便会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关中平原的夜空被照亮,直至黎明的到来,方才迟迟熄灭。
余烬未散的坑洞里,没了人的痕迹,只剩下未有完全化成灰的骨头,张汤检验过后,命令行刑吏卒掩埋。
监刑台也被拆掉,那些土全部填回了坑洞之中,刚刚好。
“从今往后,大司空你我,便是后世唾骂的‘狗官’了。”
边通踩着热土,为自己的身后名叹息。
上一个坑杀这么多人的还是秦朝武安君白起,长平一战,白起坑杀了赵国四十万降卒,为之不祥,被秦昭襄王赐死杜邮。
他莫名地觉得,自己的寿短了些。
也在担心死后,后人对主刑的自己如何评价,上君走狗?亦或是鹰犬。
正要上车架的张汤脚步一顿,回头望着他,“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我相信我之后,会有无数后人为我粉饰是非。”
作为一名纯粹的酷吏,他做了这么多事,在后世的声誉,哪怕再坏,也坏不过商鞅,他和商鞅,也会成为所有法吏的丰碑。
依然是那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言罢,张汤便上了车架,车轮辚辚驶向长安城。
“大司空,为何这么心急?”
边通望着车尾,十分不明白,只听车过之处,昂然的声音传来,“来不及了,我要去踹儒人的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