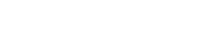一炷香的光景转瞬即逝。
蹄声踏破泥泞雨幕,
数十名身著青色劲装、神情彪悍的汉子,簇拥著马车,碾过湿滑土路,最终停在一座荒草丛生、破败倾颓的土庙前。
庙墙斑驳,瓦片零落,在沉沉的暮色里,宛如一头蛰伏的疲惫巨兽。
天光早已被厚重的乌云吞噬殆尽。
起初淅淅沥沥的冷雨,此刻已化作瓢泼之势,
豆大的雨点密集砸落,在泥地上溅起浑浊的水。
远处天际,闷雷滚滚而来,如同战鼓擂动,预示著这场豪雨,远未到停歇之时。
“下马!进庙避雨!”
为首那钟姓鏢头声如洪钟,面容刚毅,一双鹰目在雨夜中锐利如刀。
他低喝一声,率先翻身下马,冰冷的雨水瞬间浸透了他肩头的皮氅。
他带著几名心腹手下,步履沉稳地踏入了那散发著霉湿气息的庙门。
庙內空间不大,几处摇曳的篝火勉强驱散了深重的黑暗。
中央供奉的神像早已残破不堪,布满蛛网尘埃,香案也朽烂歪斜。
角落一处火堆旁,瑟缩著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约莫六七岁的男童,男人脸上刻满风霜,妇人紧搂著孩子,眼中满是惊惶。
另一侧稍远的火堆边,则静静盘坐著一名青年,身著洗得发白的粗麻布衣,身形瘦削却腰背挺直。
青年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火光映著他轮廓分明的侧脸,显得异常沉静。
显然,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將几拨赶路人都困在了这方寸之地。
钟鏢师鹰隼般的目光飞快扫过庙內眾人,尤其是在那闭目盘坐的麻衣青年身上略作停顿,眉头不易察觉地拧紧。
此行护送的鏢物非同小可,干繫著整个鏢局的声誉甚至存亡。
这荒郊野庙,鱼龙混杂,终究是心头大患。
“去,”他侧过头,对身旁一名精悍的青衣汉子低声吩咐,声音压得极低,带著不容置疑的冷硬,
“取些银钱,请那两拨人另寻他处避雨。非常之时,寧可谨慎十分,也莫要大意一分。”
“是,鏢头!”
那汉子显然深知其中利害,虽觉雨大赶人有些苛责,但不敢违命,抱拳应声。
恰在此时,庙门处一阵香风袭来,一道窈窕身影在健妇撑开的油纸伞下款款而入。
来者是一位二十出头的锦袍女子,云鬢如墨,肤光胜雪,怀中抱著一只通体雪白、毫无杂色的猫儿。
猫儿眼瞳金黄,慵懒地扫视著庙內。
女子身后,紧跟著两名身形壮硕、太阳穴微鼓、一看便是外家功夫好手的健妇,以及一位手持伞、模样伶俐的丫鬟。
(请记住????????????.??????网站,观看最快的章节更新)
“钟鏢头,”
女子声音清越,如珠落玉盘,她目光掠过那对惶恐的夫妇和角落里的青年,最终落在钟鏢师身上,唇角微扬,带著一丝不容置喙的意味,
“雨势如此滂沱,赶人未免不近人情。都是风尘僕僕的赶路人,不过求一隅避雨之所,凑合一晚罢了,待明日天色放晴,自会离去。”
“小姐心善,体恤下情。”
钟铭心中暗自嘆息,面上却不敢有丝毫怠慢,当即躬身应道,“属下遵命便是。”
这位主家小姐的性子,他深知一二,此刻再多言也是徒劳。
锦袍女子微微頷首,莲步轻移,抱著那雪白猫儿,径直走向土庙深处相对乾燥的空地。
两名健妇动作利落,迅速从行囊中取出一张厚实柔软的雪白兽皮,平整铺开。
那俏丽丫鬟则取出一个巴掌大小、古色古香的紫铜香炉,用火摺子点燃一支细长的紫色香烛插入炉中。
霎时间,
一股清冽悠远、带著安定心神之效的檀香气息,在潮湿阴冷的庙宇中悄然瀰漫开来,將雨水的土腥味和庙宇的陈腐气冲淡了不少。
钟铭並未隨侍,
他目光重新投向庙內另两拨人,脚步沉稳地朝那对夫妇走去。
见他大步逼近,
那年轻夫妇如同受惊的鸟雀,慌忙起身,男人下意识將妻儿护在身后,脸上堆满惶恐。
妇人怀中的孩童更是嚇得小脸煞白,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襟,大气不敢出。
“莫要惊慌,”
钟铭摆了摆手,儘量让语气显得平和些,“不过是例行盘问几句。姓名?籍贯?可有路引凭证?”
他目光如电,锁住那男子,同时眼角余光警惕地留意著四周动静。
“回…回鏢头老爷话,”
男子声音发颤,慌忙从怀中掏出一张摺叠整齐、油纸包裹的文书,“小人李福全,镜州城西柳树巷人士,此次是携家小回乡探望老母,这是小人的路引,请鏢头过目。”
钟铭接过路引,就著火光仔细审视。
纸张泛黄但完整,官府的硃砂大印清晰可辨,防偽暗记也一一对得上。
他又仔细看了看李福全那被生活磨礪得粗糙的面容,以及那带著浓重镜州本地口音的话语,紧绷的心弦稍稍鬆了一分。
他行走江湖多年,辨人识物自有其法,这路引和口音,不似作偽。
“嗯,確是镜州人士。”
钟铭將路引递还,语气缓和了些,“在下义安鏢局总鏢头钟铭,职责所在,方才盘查,多有得罪,还望海涵。”
说话间,他从腰间褡褳里摸出一小块约莫二两重的碎银,递了过去。
“多谢鏢头老爷!多谢老爷恩典!”
李福全一见银子,眼中闪过惊喜,连连躬身作揖,千恩万谢地领著依旧惴惴不安的妻儿,退回到角落的火堆旁。
处理完这边,钟铭锐利的目光转向另一侧。
那麻衣青年不知何时已睁开眼,平静地迎著他的视线。
那双眸子在火光映照下,竟显得格外深邃沉静,毫无寻常百姓面对他这等江湖人物时的惧色。
“这位小兄弟,”
钟铭走到青年面前三步处站定,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他抱拳一礼,目光却如探针般扫视著对方周身上下,尤其是其双手和腰腿,
“不知是何方人士?可有路引在身?”
他看似隨意,全身筋骨却已悄然绷紧。
钟姓鏢头行走江湖多年,阅人无数,眼前的这位青年,总给他一种隔阂之感。
久经锤炼的气血在四肢百骸中暗暗涌动,多年刀头舔血的本能让他对任何未知都保持著高度警惕。
“钟总鏢头有礼。”
青年起身,同样抱拳回礼,动作不疾不徐,带著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在下厉飞雨,自临江郡逃难而来,欲往镜州城投奔亲戚。”
他神色坦然,从怀中取出一份路引,双手递了过去。
蹄声踏破泥泞雨幕,
数十名身著青色劲装、神情彪悍的汉子,簇拥著马车,碾过湿滑土路,最终停在一座荒草丛生、破败倾颓的土庙前。
庙墙斑驳,瓦片零落,在沉沉的暮色里,宛如一头蛰伏的疲惫巨兽。
天光早已被厚重的乌云吞噬殆尽。
起初淅淅沥沥的冷雨,此刻已化作瓢泼之势,
豆大的雨点密集砸落,在泥地上溅起浑浊的水。
远处天际,闷雷滚滚而来,如同战鼓擂动,预示著这场豪雨,远未到停歇之时。
“下马!进庙避雨!”
为首那钟姓鏢头声如洪钟,面容刚毅,一双鹰目在雨夜中锐利如刀。
他低喝一声,率先翻身下马,冰冷的雨水瞬间浸透了他肩头的皮氅。
他带著几名心腹手下,步履沉稳地踏入了那散发著霉湿气息的庙门。
庙內空间不大,几处摇曳的篝火勉强驱散了深重的黑暗。
中央供奉的神像早已残破不堪,布满蛛网尘埃,香案也朽烂歪斜。
角落一处火堆旁,瑟缩著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约莫六七岁的男童,男人脸上刻满风霜,妇人紧搂著孩子,眼中满是惊惶。
另一侧稍远的火堆边,则静静盘坐著一名青年,身著洗得发白的粗麻布衣,身形瘦削却腰背挺直。
青年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火光映著他轮廓分明的侧脸,显得异常沉静。
显然,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將几拨赶路人都困在了这方寸之地。
钟鏢师鹰隼般的目光飞快扫过庙內眾人,尤其是在那闭目盘坐的麻衣青年身上略作停顿,眉头不易察觉地拧紧。
此行护送的鏢物非同小可,干繫著整个鏢局的声誉甚至存亡。
这荒郊野庙,鱼龙混杂,终究是心头大患。
“去,”他侧过头,对身旁一名精悍的青衣汉子低声吩咐,声音压得极低,带著不容置疑的冷硬,
“取些银钱,请那两拨人另寻他处避雨。非常之时,寧可谨慎十分,也莫要大意一分。”
“是,鏢头!”
那汉子显然深知其中利害,虽觉雨大赶人有些苛责,但不敢违命,抱拳应声。
恰在此时,庙门处一阵香风袭来,一道窈窕身影在健妇撑开的油纸伞下款款而入。
来者是一位二十出头的锦袍女子,云鬢如墨,肤光胜雪,怀中抱著一只通体雪白、毫无杂色的猫儿。
猫儿眼瞳金黄,慵懒地扫视著庙內。
女子身后,紧跟著两名身形壮硕、太阳穴微鼓、一看便是外家功夫好手的健妇,以及一位手持伞、模样伶俐的丫鬟。
(请记住????????????.??????网站,观看最快的章节更新)
“钟鏢头,”
女子声音清越,如珠落玉盘,她目光掠过那对惶恐的夫妇和角落里的青年,最终落在钟鏢师身上,唇角微扬,带著一丝不容置喙的意味,
“雨势如此滂沱,赶人未免不近人情。都是风尘僕僕的赶路人,不过求一隅避雨之所,凑合一晚罢了,待明日天色放晴,自会离去。”
“小姐心善,体恤下情。”
钟铭心中暗自嘆息,面上却不敢有丝毫怠慢,当即躬身应道,“属下遵命便是。”
这位主家小姐的性子,他深知一二,此刻再多言也是徒劳。
锦袍女子微微頷首,莲步轻移,抱著那雪白猫儿,径直走向土庙深处相对乾燥的空地。
两名健妇动作利落,迅速从行囊中取出一张厚实柔软的雪白兽皮,平整铺开。
那俏丽丫鬟则取出一个巴掌大小、古色古香的紫铜香炉,用火摺子点燃一支细长的紫色香烛插入炉中。
霎时间,
一股清冽悠远、带著安定心神之效的檀香气息,在潮湿阴冷的庙宇中悄然瀰漫开来,將雨水的土腥味和庙宇的陈腐气冲淡了不少。
钟铭並未隨侍,
他目光重新投向庙內另两拨人,脚步沉稳地朝那对夫妇走去。
见他大步逼近,
那年轻夫妇如同受惊的鸟雀,慌忙起身,男人下意识將妻儿护在身后,脸上堆满惶恐。
妇人怀中的孩童更是嚇得小脸煞白,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襟,大气不敢出。
“莫要惊慌,”
钟铭摆了摆手,儘量让语气显得平和些,“不过是例行盘问几句。姓名?籍贯?可有路引凭证?”
他目光如电,锁住那男子,同时眼角余光警惕地留意著四周动静。
“回…回鏢头老爷话,”
男子声音发颤,慌忙从怀中掏出一张摺叠整齐、油纸包裹的文书,“小人李福全,镜州城西柳树巷人士,此次是携家小回乡探望老母,这是小人的路引,请鏢头过目。”
钟铭接过路引,就著火光仔细审视。
纸张泛黄但完整,官府的硃砂大印清晰可辨,防偽暗记也一一对得上。
他又仔细看了看李福全那被生活磨礪得粗糙的面容,以及那带著浓重镜州本地口音的话语,紧绷的心弦稍稍鬆了一分。
他行走江湖多年,辨人识物自有其法,这路引和口音,不似作偽。
“嗯,確是镜州人士。”
钟铭將路引递还,语气缓和了些,“在下义安鏢局总鏢头钟铭,职责所在,方才盘查,多有得罪,还望海涵。”
说话间,他从腰间褡褳里摸出一小块约莫二两重的碎银,递了过去。
“多谢鏢头老爷!多谢老爷恩典!”
李福全一见银子,眼中闪过惊喜,连连躬身作揖,千恩万谢地领著依旧惴惴不安的妻儿,退回到角落的火堆旁。
处理完这边,钟铭锐利的目光转向另一侧。
那麻衣青年不知何时已睁开眼,平静地迎著他的视线。
那双眸子在火光映照下,竟显得格外深邃沉静,毫无寻常百姓面对他这等江湖人物时的惧色。
“这位小兄弟,”
钟铭走到青年面前三步处站定,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他抱拳一礼,目光却如探针般扫视著对方周身上下,尤其是其双手和腰腿,
“不知是何方人士?可有路引在身?”
他看似隨意,全身筋骨却已悄然绷紧。
钟姓鏢头行走江湖多年,阅人无数,眼前的这位青年,总给他一种隔阂之感。
久经锤炼的气血在四肢百骸中暗暗涌动,多年刀头舔血的本能让他对任何未知都保持著高度警惕。
“钟总鏢头有礼。”
青年起身,同样抱拳回礼,动作不疾不徐,带著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在下厉飞雨,自临江郡逃难而来,欲往镜州城投奔亲戚。”
他神色坦然,从怀中取出一份路引,双手递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