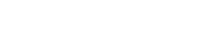第192章 集权
参预国事?
一言落点,举殿惊讶。
失去了诸侯王权,却成了“王大臣”,直接就理国事,虽然没有决策权,但对全国朝政、军国大事予以监督,甚至拥有随时奏上的权力。
王公们的心,莫名地有点热。
要知道,臣子是不能随意面圣的,除了诏见,便是觐见,是以,见圣为殊。
这是份荣耀。
也是份权力!
随时见圣,随时参奏,随时都有可能让一人乃至一国发生变化。
一语乾坤变,从古至今有几人啊?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王大臣的参政、议政权力乃君主赐予,以上君为例,可以随时收回楚王刘注、河间王刘基的王大臣头衔,罢撤两人所有在朝权力。
怎么说呢,像是皇权的延伸。
用以侵蚀相权。
这像是在丞相身边安插了两个监察,做事时、决策时,丞相必须要比以前更加慎重。
诸侯王们和中外两朝公卿、列侯、宗室大臣不由得望向了丞相公孙弘,却见他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想想也是啊,在陛下执政时期,陛下为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开始依靠身边的亲信近臣来参与重大决策,以此形成了中外朝制。
这使得原本由丞相掌握的决策权逐渐转移到中朝官员手中,大汉丞相的权力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陛下明显是奔着让外朝丞相以后成为泥塑、木雕去的。
也就是丞相府毅然决然选择了上君,为上君执政铺平了道路,在上君执政以后,既是为了打击陛下的权力,又是为了投桃报李,再次增加了丞相的权力。
现在,上君南征北战,靠着卫青、霍去病、张次公、路博德等人,建立了万世之功的武功盛德,又通过公孙弘、张汤等人,推动了大汉制度的文治变革,更压迫了陛下为数不多的权力,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上君手中,接着对相权动手,不是多么出人意料的事。
近乎“成精”的老丞相,想必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不但不会反对,甚而可能还会予以支持。
一片嚷嚷中,王公们都愣怔了,逐渐默然了下来。
少君、老相,本来是很不稳定的权力结构,但上君和老丞相却十分契合。
或许,这就是“君臣一体”吧。
刘注、刘基尚在对上君手笔而动容中,城阳王刘彭离、甾川王刘建、济北王刘胡等十王,一个个激动道:“臣也愿意上交王府三护卫,入长安王宅,自请为王大臣!”
“臣愿意!”
“臣也愿意!”
“……”
宣室殿上,城阳十王争的面红耳赤。
为诸侯王时,整日胆战心惊,恐惧削藩旨意到达。
为王大臣时,俨然君主化身,不为君主怀疑、忌惮,反受君主信任、放心,不会被朝臣参奏,还能参奏朝臣,登堂入室,自由行走于天下,这才更像是次于皇权的王权。
诸侯王们这见好处就上的模样,着实震惊了中外两朝文武,这群王者,当真是一点颜面都不要了。
连御座之上的刘据都沉默了。
楚王、河间王的罪过,是为了让君主、朝廷放心的故意为之。
城阳十王的罪过,是欺男霸女、是为祸一方的故意为之。
两个“故意为之”能一样吗?
不先想着脱罪,伸手就要头衔,要权力。
刘据忽然想到一个对城阳十王贴切的形容,“见小利而忘命,干大事而惜身,色厉胆薄,好谋无断”。
一条新路,第一个走的是天才,第二个走的是庸才,第三个走的是蠢才,第四个就要入棺材了。
城阳十王,就是十个要入棺材的蠢货!
刘据望向了张汤。
龙目注视。
张汤立刻有了动作,望向城阳十王,呵斥道:“放肆!”
一股凌厉的气势,顿时笼罩了城阳十王,大殿中一时肃然无声。
在诸侯王没有被问罪前,仍是大汉的宗王,张汤即便贵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也是大汉的臣子,以臣喝王,可谓不敬。
城阳十王愣了下,随后便回过了神,满腔愤怒涌上心头,刚欲爆发,张汤抢先道:“尔等高祖血脉,不思敬天法祖,为国分忧,自就藩以来,国中礼崩乐坏,瓦釜雷鸣,最终酿得天怒人怨,朝野沸腾。
大汉治式之变,上君有意结束裂土而治,避免天下动荡不休,人心思治,人心思一,思的便是天下一统,思的便是一法施治,思的便是抛却尔等。
尔等犹不加悔改,不知惭愧,主动上奏请罪,自请废爵,潜心读书,犹加以恋栈,嗜权如命。
今日之天下,若用尔等为参政议政王大臣,无异于抛离天下民心,无异于再行裂土分治之根,恐大汉国事百年而未有一致焉!
尔等铸下大罪而不请罪,难不是欺我上君宽恕多仁邪?”
一番大骂,城阳十王未必能听得懂,但末了那个“欺君”却是听懂了,忙说道:“绝无此意!”
“既如此,还不请罪!”张汤丝毫不为所动,冷冷道。
中外两朝官吏一片愤怒呵斥,“还不请罪!”
滔滔之声,使得渐渐闷热起来的大殿如秋风扫过,肃杀气息顿生,吓得城阳十王肝胆俱颤。
同为诸侯王,上君、群臣所予楚王、河间王,他们的态度和礼遇怎么不一样呢?
君臣之威浩荡,城阳十王无可奈何低下了头,再次朝向御座跪倒,齐声道:“臣等有罪!”
憋屈至极。
张汤望向刘注、刘基,皱眉道:“二位殿下,还不谢恩?”
参政议政王大臣似无实权却又极为要害,人越少权力越大,不知道楚王、河间王在发什么愣。
刘注、刘基朝张汤投去了谢意的目光,而后再次大拜道:“臣谢过上君隆恩!”
“起来吧。”
刘据望向了公孙弘,“老相国,寡人的两位族亲,就交给你了。”
公孙弘缓缓从绣墩上站起,躬身下拜道:“臣必当与二位王大臣同心协力国政,不负上君托付。”
刘据颔首,望向城阳十王,失去了所有耐心,“交出王府三护卫,入长安王宅读书,既往不咎。”
“是,上君。”
(本章完)
参预国事?
一言落点,举殿惊讶。
失去了诸侯王权,却成了“王大臣”,直接就理国事,虽然没有决策权,但对全国朝政、军国大事予以监督,甚至拥有随时奏上的权力。
王公们的心,莫名地有点热。
要知道,臣子是不能随意面圣的,除了诏见,便是觐见,是以,见圣为殊。
这是份荣耀。
也是份权力!
随时见圣,随时参奏,随时都有可能让一人乃至一国发生变化。
一语乾坤变,从古至今有几人啊?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王大臣的参政、议政权力乃君主赐予,以上君为例,可以随时收回楚王刘注、河间王刘基的王大臣头衔,罢撤两人所有在朝权力。
怎么说呢,像是皇权的延伸。
用以侵蚀相权。
这像是在丞相身边安插了两个监察,做事时、决策时,丞相必须要比以前更加慎重。
诸侯王们和中外两朝公卿、列侯、宗室大臣不由得望向了丞相公孙弘,却见他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想想也是啊,在陛下执政时期,陛下为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开始依靠身边的亲信近臣来参与重大决策,以此形成了中外朝制。
这使得原本由丞相掌握的决策权逐渐转移到中朝官员手中,大汉丞相的权力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陛下明显是奔着让外朝丞相以后成为泥塑、木雕去的。
也就是丞相府毅然决然选择了上君,为上君执政铺平了道路,在上君执政以后,既是为了打击陛下的权力,又是为了投桃报李,再次增加了丞相的权力。
现在,上君南征北战,靠着卫青、霍去病、张次公、路博德等人,建立了万世之功的武功盛德,又通过公孙弘、张汤等人,推动了大汉制度的文治变革,更压迫了陛下为数不多的权力,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上君手中,接着对相权动手,不是多么出人意料的事。
近乎“成精”的老丞相,想必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不但不会反对,甚而可能还会予以支持。
一片嚷嚷中,王公们都愣怔了,逐渐默然了下来。
少君、老相,本来是很不稳定的权力结构,但上君和老丞相却十分契合。
或许,这就是“君臣一体”吧。
刘注、刘基尚在对上君手笔而动容中,城阳王刘彭离、甾川王刘建、济北王刘胡等十王,一个个激动道:“臣也愿意上交王府三护卫,入长安王宅,自请为王大臣!”
“臣愿意!”
“臣也愿意!”
“……”
宣室殿上,城阳十王争的面红耳赤。
为诸侯王时,整日胆战心惊,恐惧削藩旨意到达。
为王大臣时,俨然君主化身,不为君主怀疑、忌惮,反受君主信任、放心,不会被朝臣参奏,还能参奏朝臣,登堂入室,自由行走于天下,这才更像是次于皇权的王权。
诸侯王们这见好处就上的模样,着实震惊了中外两朝文武,这群王者,当真是一点颜面都不要了。
连御座之上的刘据都沉默了。
楚王、河间王的罪过,是为了让君主、朝廷放心的故意为之。
城阳十王的罪过,是欺男霸女、是为祸一方的故意为之。
两个“故意为之”能一样吗?
不先想着脱罪,伸手就要头衔,要权力。
刘据忽然想到一个对城阳十王贴切的形容,“见小利而忘命,干大事而惜身,色厉胆薄,好谋无断”。
一条新路,第一个走的是天才,第二个走的是庸才,第三个走的是蠢才,第四个就要入棺材了。
城阳十王,就是十个要入棺材的蠢货!
刘据望向了张汤。
龙目注视。
张汤立刻有了动作,望向城阳十王,呵斥道:“放肆!”
一股凌厉的气势,顿时笼罩了城阳十王,大殿中一时肃然无声。
在诸侯王没有被问罪前,仍是大汉的宗王,张汤即便贵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也是大汉的臣子,以臣喝王,可谓不敬。
城阳十王愣了下,随后便回过了神,满腔愤怒涌上心头,刚欲爆发,张汤抢先道:“尔等高祖血脉,不思敬天法祖,为国分忧,自就藩以来,国中礼崩乐坏,瓦釜雷鸣,最终酿得天怒人怨,朝野沸腾。
大汉治式之变,上君有意结束裂土而治,避免天下动荡不休,人心思治,人心思一,思的便是天下一统,思的便是一法施治,思的便是抛却尔等。
尔等犹不加悔改,不知惭愧,主动上奏请罪,自请废爵,潜心读书,犹加以恋栈,嗜权如命。
今日之天下,若用尔等为参政议政王大臣,无异于抛离天下民心,无异于再行裂土分治之根,恐大汉国事百年而未有一致焉!
尔等铸下大罪而不请罪,难不是欺我上君宽恕多仁邪?”
一番大骂,城阳十王未必能听得懂,但末了那个“欺君”却是听懂了,忙说道:“绝无此意!”
“既如此,还不请罪!”张汤丝毫不为所动,冷冷道。
中外两朝官吏一片愤怒呵斥,“还不请罪!”
滔滔之声,使得渐渐闷热起来的大殿如秋风扫过,肃杀气息顿生,吓得城阳十王肝胆俱颤。
同为诸侯王,上君、群臣所予楚王、河间王,他们的态度和礼遇怎么不一样呢?
君臣之威浩荡,城阳十王无可奈何低下了头,再次朝向御座跪倒,齐声道:“臣等有罪!”
憋屈至极。
张汤望向刘注、刘基,皱眉道:“二位殿下,还不谢恩?”
参政议政王大臣似无实权却又极为要害,人越少权力越大,不知道楚王、河间王在发什么愣。
刘注、刘基朝张汤投去了谢意的目光,而后再次大拜道:“臣谢过上君隆恩!”
“起来吧。”
刘据望向了公孙弘,“老相国,寡人的两位族亲,就交给你了。”
公孙弘缓缓从绣墩上站起,躬身下拜道:“臣必当与二位王大臣同心协力国政,不负上君托付。”
刘据颔首,望向城阳十王,失去了所有耐心,“交出王府三护卫,入长安王宅读书,既往不咎。”
“是,上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