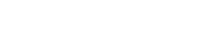第193章 嬗变
廷议毕。
诸侯王和中外两朝公卿、列侯、宗室大臣退殿。
丞相公孙弘留了下来。
望着霞光中逐渐消失的王公背影,刘据从御座而下,公孙弘立刻就要起身,却被阻止了,“老相国,坐下说。”
绛伯为刘据搬来了绣墩,君臣对面而坐,刘据率先开口道:“参政议政王大臣的设立,寡人希望老相国不要误会。”
的确是为了削弱相权。
但不是针对公孙弘。
“臣没有误会。”
公孙弘摇摇头,混浊的目光中时常有精光闪烁,发自内心道:“从古至今,君权和相权,或者与公卿大夫的权力,在博弈,在搏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上君能做到这种地步,臣已是感激涕零、铭感五内了。”
这个人间,是个巨大的矛盾体。
君主专制需要官僚组织提高统治效益,但又排斥其自主性,这就导致了矛盾产生。
君权多代表个人私利,相权多代表官僚组织整体利益,两者在利益分配和政令制定上,往往存在重大分歧。
在施政重点上,君主倾向于个人意志,而丞相及其官僚组织从整体利益出发,制约或矫正君权。
有人的地方,就有私心。
君主希望乾坤独断,而丞相希望官僚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是制衡皇权。
历朝历代的君主、丞相、公卿大夫始终在为各自的权力斗争,君臣的权力,一直是“此消彼长”的态势。
成为大汉丞相的数年间,公孙弘的感受越来越清晰,帝国需要集权,也需要一名君主能主宰大汉,拖着朝廷走向更远。
分歧,只会导致混乱,混乱,只会导致灭亡。
当然,大汉帝国不需要陛下那般穷奢极欲的“独夫”。
要的是上君这样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圣主贤君。
“不过,臣要提醒上君,过度削弱相权,反而会导致国家政务、军国大事处理缓慢,如果分权过细,自我消耗,长此以往,帝国必将积弱积贫。”公孙弘缓缓说道。
相权可以削弱,如上君在丞相府增添了两位参政议政王大臣,这样,丞相政务不当时,王大臣便能提出异议,这是很好的。
但如果在廷议上,上君同意了城阳十王都为参政议政王大臣,过多的人参预国事,反而就不好了。
人多,想法就多,考虑的事情就多,你不满意我的想法,我也不同意你的提请,一来二去,该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都没办法办,党同伐异,彼此消磨,国事便耽搁了,帝国也会往弱、贫的方向滑坡。
刘据点点头,“寡人明白。”
公孙弘犹豫了下,叹了口气道:“上君心中,或许有对相权变革的草案准备了吧?”
刘据一惊,倒也没有隐瞒,再次点点头,“寡人从未予人言,不成想被老相国看出来的,相国大智慧也。”
“秦法吏所创之制,为我汉法吏所效仿,但我汉君并非秦君,今日之天下,也非昨日之秦廷,过去引以为绝制的创制,今朝便显得不足了,上君远见卓识,想为之改动,臣以为没有不妥,但要慎之又慎。”公孙弘郑重道。
现行制度,脱不开秦制,而秦制是秦相李斯根据始皇帝所定制。
以郡县一治为根基,以集权求治为宗旨,以施政治民为侧重,以治权集于中央为轴心,从上到下建立的一套完整施政体系。
这一施政体系分为四级,层层辖制,从皇帝宫殿到村畴乡野,一体纳入治道。
简言之,中央决策以皇帝为中心,中央政务以丞相为轴心,地方施政交托郡守县令,乡官基层交给民治。
如上四大体系,非但在战国末世堪称宏大奇迹,即或在今日、未来看去,永远不会过时。
帝国对施政体系的四层级分割——国、郡、县、乡,能让前人、今人、后人叹为观止。
但是,秦始皇帝嬴政、大秦法相李斯却忽略了个最关键的问题。
稳定!
以法家思想治国,崇尚以暴制暴的秦廷君臣,没能及时转变帝国纲领,再加上对惹是生非的六国余孽太过宽容,使得始皇帝一死,大秦立时大乱。
秦廷得了“暴秦”之名,秦始皇帝也成了“暴君”、“独夫”。
上君、卫青、霍去病、他、张汤的君臣组合,可以在本朝推行任何可行的制度,也可以用任何思想作为治国纲领,五人之中,只要有一人尚在,大汉就亡不了。
问题是,五人相继百年之后,大汉会不会重蹈秦廷覆辙。
上君意欲对四大施政体系中的关键位置,上接君意,下领臣民的相权变革,稍有不慎,就可能埋下亡国的祸根。
上君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显著纲纪,改动相权,如果影响了稳定,那不如不改。
昙刹那芳华再美,也不如牡丹长久国色天香。
刘据躁动的心缓和了许多,认可道:“老相国所言极是。”
“臣老了,入夏以来,时常觉得倦怠无有精神,身体沉沉,恐将一日一睡不醒。”
公孙弘述说着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季节的原因,是真的接近油尽灯枯了,现在的每一日,都可能是他的寿终之日,“上君年少,有大把的岁月,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超越孝文帝、超越高皇帝、超越尧舜禹汤……把大汉的光芒洒向更遥远的地方,臣想说,慢慢来,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上君,您已经做的很好了,比过去的任何人、任何君主还要好!”
公孙弘眼睛里满是遗憾,上君来时,他都八十了,如果再早二十年、四十年,那该多好啊。
刘据握住公孙弘那如同枯枝的手,重重地点头,牢记国臣的肺腑之言。
“上君,李家将灭,领兵在匈奴左翼的李广、李敢、李陵三代人,必然难以回国授首,要做好他们携军叛逃的准备。”公孙弘近乎絮叨交代了廷议之中的未尽之事。
刘据悉数记下,亲送老相国出殿,望着他的背影,“拟诏,晋丞相公孙弘为太傅!”
(本章完)
廷议毕。
诸侯王和中外两朝公卿、列侯、宗室大臣退殿。
丞相公孙弘留了下来。
望着霞光中逐渐消失的王公背影,刘据从御座而下,公孙弘立刻就要起身,却被阻止了,“老相国,坐下说。”
绛伯为刘据搬来了绣墩,君臣对面而坐,刘据率先开口道:“参政议政王大臣的设立,寡人希望老相国不要误会。”
的确是为了削弱相权。
但不是针对公孙弘。
“臣没有误会。”
公孙弘摇摇头,混浊的目光中时常有精光闪烁,发自内心道:“从古至今,君权和相权,或者与公卿大夫的权力,在博弈,在搏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上君能做到这种地步,臣已是感激涕零、铭感五内了。”
这个人间,是个巨大的矛盾体。
君主专制需要官僚组织提高统治效益,但又排斥其自主性,这就导致了矛盾产生。
君权多代表个人私利,相权多代表官僚组织整体利益,两者在利益分配和政令制定上,往往存在重大分歧。
在施政重点上,君主倾向于个人意志,而丞相及其官僚组织从整体利益出发,制约或矫正君权。
有人的地方,就有私心。
君主希望乾坤独断,而丞相希望官僚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是制衡皇权。
历朝历代的君主、丞相、公卿大夫始终在为各自的权力斗争,君臣的权力,一直是“此消彼长”的态势。
成为大汉丞相的数年间,公孙弘的感受越来越清晰,帝国需要集权,也需要一名君主能主宰大汉,拖着朝廷走向更远。
分歧,只会导致混乱,混乱,只会导致灭亡。
当然,大汉帝国不需要陛下那般穷奢极欲的“独夫”。
要的是上君这样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圣主贤君。
“不过,臣要提醒上君,过度削弱相权,反而会导致国家政务、军国大事处理缓慢,如果分权过细,自我消耗,长此以往,帝国必将积弱积贫。”公孙弘缓缓说道。
相权可以削弱,如上君在丞相府增添了两位参政议政王大臣,这样,丞相政务不当时,王大臣便能提出异议,这是很好的。
但如果在廷议上,上君同意了城阳十王都为参政议政王大臣,过多的人参预国事,反而就不好了。
人多,想法就多,考虑的事情就多,你不满意我的想法,我也不同意你的提请,一来二去,该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都没办法办,党同伐异,彼此消磨,国事便耽搁了,帝国也会往弱、贫的方向滑坡。
刘据点点头,“寡人明白。”
公孙弘犹豫了下,叹了口气道:“上君心中,或许有对相权变革的草案准备了吧?”
刘据一惊,倒也没有隐瞒,再次点点头,“寡人从未予人言,不成想被老相国看出来的,相国大智慧也。”
“秦法吏所创之制,为我汉法吏所效仿,但我汉君并非秦君,今日之天下,也非昨日之秦廷,过去引以为绝制的创制,今朝便显得不足了,上君远见卓识,想为之改动,臣以为没有不妥,但要慎之又慎。”公孙弘郑重道。
现行制度,脱不开秦制,而秦制是秦相李斯根据始皇帝所定制。
以郡县一治为根基,以集权求治为宗旨,以施政治民为侧重,以治权集于中央为轴心,从上到下建立的一套完整施政体系。
这一施政体系分为四级,层层辖制,从皇帝宫殿到村畴乡野,一体纳入治道。
简言之,中央决策以皇帝为中心,中央政务以丞相为轴心,地方施政交托郡守县令,乡官基层交给民治。
如上四大体系,非但在战国末世堪称宏大奇迹,即或在今日、未来看去,永远不会过时。
帝国对施政体系的四层级分割——国、郡、县、乡,能让前人、今人、后人叹为观止。
但是,秦始皇帝嬴政、大秦法相李斯却忽略了个最关键的问题。
稳定!
以法家思想治国,崇尚以暴制暴的秦廷君臣,没能及时转变帝国纲领,再加上对惹是生非的六国余孽太过宽容,使得始皇帝一死,大秦立时大乱。
秦廷得了“暴秦”之名,秦始皇帝也成了“暴君”、“独夫”。
上君、卫青、霍去病、他、张汤的君臣组合,可以在本朝推行任何可行的制度,也可以用任何思想作为治国纲领,五人之中,只要有一人尚在,大汉就亡不了。
问题是,五人相继百年之后,大汉会不会重蹈秦廷覆辙。
上君意欲对四大施政体系中的关键位置,上接君意,下领臣民的相权变革,稍有不慎,就可能埋下亡国的祸根。
上君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显著纲纪,改动相权,如果影响了稳定,那不如不改。
昙刹那芳华再美,也不如牡丹长久国色天香。
刘据躁动的心缓和了许多,认可道:“老相国所言极是。”
“臣老了,入夏以来,时常觉得倦怠无有精神,身体沉沉,恐将一日一睡不醒。”
公孙弘述说着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季节的原因,是真的接近油尽灯枯了,现在的每一日,都可能是他的寿终之日,“上君年少,有大把的岁月,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超越孝文帝、超越高皇帝、超越尧舜禹汤……把大汉的光芒洒向更遥远的地方,臣想说,慢慢来,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上君,您已经做的很好了,比过去的任何人、任何君主还要好!”
公孙弘眼睛里满是遗憾,上君来时,他都八十了,如果再早二十年、四十年,那该多好啊。
刘据握住公孙弘那如同枯枝的手,重重地点头,牢记国臣的肺腑之言。
“上君,李家将灭,领兵在匈奴左翼的李广、李敢、李陵三代人,必然难以回国授首,要做好他们携军叛逃的准备。”公孙弘近乎絮叨交代了廷议之中的未尽之事。
刘据悉数记下,亲送老相国出殿,望着他的背影,“拟诏,晋丞相公孙弘为太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