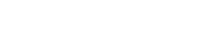第199章 卧龙
一叶知秋。
董仲舒望着翻飞的楸树树叶,伸出了手掌,也许是受到病体拖延,手未至,叶已落。
忽然间,唏嘘泪下。
“老师,天凉了。”
吾丘寿王走了过来,为董仲舒披上了件大氅,轻声道。
从得知王公廷议内容那日起,董仲舒便病至而今,难有起时。
但见老师重新打起精神,出外欣赏秋景,吾丘寿王难得松了口气。
董仲舒沉默良久,喟然一叹道:“何止是天凉了。”
人心更凉。
十数代儒者的努力,终于看到了团锦簇,知道了灯彩佳话,转眼间,尽成泡影。
宛如昙一现。
这对董仲舒的伤害,反而比漫长的“黑暗时代”更大。
没有看过光明的人,是可以忍受黑暗的,无法忍受的是,光芒万丈后的无尽黑暗。
董仲舒眼前的色彩逐渐黯淡,只留下黑白两色。
“我不起的这段时间,大汉又发生了哪些大事?”
“老师……”
“无妨,我撑得住。”
吾丘寿王斟酌了下措辞,试图寻找委婉的说法,但发现没有什么委婉的余地,由近及远道:“广川那里传来消息,族中遭到‘共功’,老师的诸多著作,如《春秋繁露》、《春秋决事比》等书,已经失落。”
广川是董仲舒的老家,董族也是当地的望门,人人以儒士标榜自身,在共功制下,偌大的董族被毁,连宗祠都没有放过,董族历代祖宗的神主牌也被砸毁后烧了。
片瓦不留。
董族几名族老当场气死,其他族人,包括董仲舒的亲眷,栖身在神祇庙中,才避免了流落街头。
“陛下得知之后,特派使者前去广川,为老师的亲眷、族人解决食宿之事。”吾丘寿王补充道。
对待心腹,陛下很多时候还是当人的,尤其是被困于南阳,上君限制了陛下所有高额靡费行为后,窦太主、平阳公主两位大汉长公主送到这里的钱财珍宝,陛下没有了挥霍的地方,更愿意赏赐出去,以邀买人心。
效果不错,南巡五百人及附近郡县百姓,逐渐对皇帝的形象具体化,至少在这里,陛下圣誉不错。
陛下兴高采烈之余,金口改了此地地名,曰:“卧龙岗”,上报朝廷后,得到了上君的允准。
现在上君的态度,南巡君臣基本摸清了,只要陛下不把钱财靡费在龙躯上,想怎么赏赐出去都可以。
所以,陛下整日吃着锅盔野菜,他们这群臣民却能时常有荤腥。
此次“赏董”,陛下直接宣布包了董族之人以后的食宿,不是不想赏赐更多,而是赏赐多了董族也留不住。
董仲舒强撑着站起身,向着龙帐方向一拜到地,“圣皇恩德,铭记在心。”
礼毕,吾丘寿王连忙扶他坐下,继续道:“中外两朝的儒家官吏,也在共功制下穷困潦倒,以致于堂堂中朝大夫,只能靠多吃官署食物充饥,靠多占官署食物填饱妻儿老小肚腹,引以为天下笑柄。”
这说的自然是中大夫儿宽了,整个儿府被愤怒的百家中人不但被夷为平地,而且,百家还派出子弟专门盯着,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出现在儿家,就立刻会有人抢……共功。
作为大汉官吏,儿宽是有俸禄的,可这部分钱粮也在丞相府默许下,不经过儿宽之手便没了。
为了不被饿死,也为了不上街乞讨,儿宽只有靠官署食物来维持自己和家眷存活。
董仲舒对儿宽没有怨恨,知道儿宽只是儒家劫难的引子而已,儿宽没有自戕,也不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其他儒者。
一旦儿宽死了,腾出手的百家中人会针对更多儒者,每活一日,都是赎罪。
“陛下那里?”
“尝试了送予食宿,没有成功,最后是窦太主、平阳公主出手,以奴仆的身份将儿家人收入府中,免了餐风露宿。”吾丘寿王悲痛道。
中朝高官,竟然要通过卖儿卖女,让自己儿女成为他人奴仆的方式,才能使之活下去。
物伤其类,秋鸣也悲。
同为儒官,吾丘寿王闻之心伤,董仲舒一时无言,儿宽的遭遇,除了百家的报复,也有太子宫卿对廷议之上儿宽试图抹去上君武功盛德,大将军、冠军侯万世之功的惩戒。
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负责。
其实,上君很是仁慈了,被欺君犯上没有动手杀人,便盛过古往今来君主无数。
但这份仁慈,绝对不是重视颜面的儒士想要的,对儿宽来说,眼下的生活,生不如死。
“儒家遭逢强权肆虐、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自祖师孔夫子起,奔波列国数百年,纵秦汉两朝,终究未遇文明之邦一展抱负,大汉气象,为师也看不懂,修文重武、百齐放。”
董仲舒始终想不明白上君为何宁愿费劲手段、心力重塑华夏思想,也不愿意让“整合”了华夏思想,甚至是更加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大放光明,“然则,大汉朝廷推崇强力,借重法家兵家,对我儒家多有打压,鲜能重任。
陛下虽说对我敬重有加,自即位起便多次崇儒尝试,但是,只以我门为驭民之用,今逢上君弃之如敝履,我门日后究竟能否作为大汉,乃至华夏根基,目下尚很难说。
究其竟,儒家是尚古复礼之学,是盛世安邦之学,是教化民众之学,是修身齐家之学,是克己正身之学,惟其如此,也是生不逢时之学。
时也势也,我儒家将有一段漫漫低谷,我门同人一定要强毅精神,受的起冷遇,要像墨家那般刻苦自励,方能复兴儒家于盛世之时。”
董仲舒只好把这一切都归结于陛下、上君是力求开拓的君主,将希望寄托于后世的守成之君,望着吾丘寿王,悲壮说道:“子赣须谨记圣人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弟子谨记!”
吾丘寿王被老师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整顿了心情,继续道:“对了,老师,至圣世家传来消息,已然举族西狩南阳……”
话没说完,董仲舒便上演了出医道奇迹,跳起打断,“你说什么?”
(本章完)
一叶知秋。
董仲舒望着翻飞的楸树树叶,伸出了手掌,也许是受到病体拖延,手未至,叶已落。
忽然间,唏嘘泪下。
“老师,天凉了。”
吾丘寿王走了过来,为董仲舒披上了件大氅,轻声道。
从得知王公廷议内容那日起,董仲舒便病至而今,难有起时。
但见老师重新打起精神,出外欣赏秋景,吾丘寿王难得松了口气。
董仲舒沉默良久,喟然一叹道:“何止是天凉了。”
人心更凉。
十数代儒者的努力,终于看到了团锦簇,知道了灯彩佳话,转眼间,尽成泡影。
宛如昙一现。
这对董仲舒的伤害,反而比漫长的“黑暗时代”更大。
没有看过光明的人,是可以忍受黑暗的,无法忍受的是,光芒万丈后的无尽黑暗。
董仲舒眼前的色彩逐渐黯淡,只留下黑白两色。
“我不起的这段时间,大汉又发生了哪些大事?”
“老师……”
“无妨,我撑得住。”
吾丘寿王斟酌了下措辞,试图寻找委婉的说法,但发现没有什么委婉的余地,由近及远道:“广川那里传来消息,族中遭到‘共功’,老师的诸多著作,如《春秋繁露》、《春秋决事比》等书,已经失落。”
广川是董仲舒的老家,董族也是当地的望门,人人以儒士标榜自身,在共功制下,偌大的董族被毁,连宗祠都没有放过,董族历代祖宗的神主牌也被砸毁后烧了。
片瓦不留。
董族几名族老当场气死,其他族人,包括董仲舒的亲眷,栖身在神祇庙中,才避免了流落街头。
“陛下得知之后,特派使者前去广川,为老师的亲眷、族人解决食宿之事。”吾丘寿王补充道。
对待心腹,陛下很多时候还是当人的,尤其是被困于南阳,上君限制了陛下所有高额靡费行为后,窦太主、平阳公主两位大汉长公主送到这里的钱财珍宝,陛下没有了挥霍的地方,更愿意赏赐出去,以邀买人心。
效果不错,南巡五百人及附近郡县百姓,逐渐对皇帝的形象具体化,至少在这里,陛下圣誉不错。
陛下兴高采烈之余,金口改了此地地名,曰:“卧龙岗”,上报朝廷后,得到了上君的允准。
现在上君的态度,南巡君臣基本摸清了,只要陛下不把钱财靡费在龙躯上,想怎么赏赐出去都可以。
所以,陛下整日吃着锅盔野菜,他们这群臣民却能时常有荤腥。
此次“赏董”,陛下直接宣布包了董族之人以后的食宿,不是不想赏赐更多,而是赏赐多了董族也留不住。
董仲舒强撑着站起身,向着龙帐方向一拜到地,“圣皇恩德,铭记在心。”
礼毕,吾丘寿王连忙扶他坐下,继续道:“中外两朝的儒家官吏,也在共功制下穷困潦倒,以致于堂堂中朝大夫,只能靠多吃官署食物充饥,靠多占官署食物填饱妻儿老小肚腹,引以为天下笑柄。”
这说的自然是中大夫儿宽了,整个儿府被愤怒的百家中人不但被夷为平地,而且,百家还派出子弟专门盯着,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出现在儿家,就立刻会有人抢……共功。
作为大汉官吏,儿宽是有俸禄的,可这部分钱粮也在丞相府默许下,不经过儿宽之手便没了。
为了不被饿死,也为了不上街乞讨,儿宽只有靠官署食物来维持自己和家眷存活。
董仲舒对儿宽没有怨恨,知道儿宽只是儒家劫难的引子而已,儿宽没有自戕,也不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其他儒者。
一旦儿宽死了,腾出手的百家中人会针对更多儒者,每活一日,都是赎罪。
“陛下那里?”
“尝试了送予食宿,没有成功,最后是窦太主、平阳公主出手,以奴仆的身份将儿家人收入府中,免了餐风露宿。”吾丘寿王悲痛道。
中朝高官,竟然要通过卖儿卖女,让自己儿女成为他人奴仆的方式,才能使之活下去。
物伤其类,秋鸣也悲。
同为儒官,吾丘寿王闻之心伤,董仲舒一时无言,儿宽的遭遇,除了百家的报复,也有太子宫卿对廷议之上儿宽试图抹去上君武功盛德,大将军、冠军侯万世之功的惩戒。
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负责。
其实,上君很是仁慈了,被欺君犯上没有动手杀人,便盛过古往今来君主无数。
但这份仁慈,绝对不是重视颜面的儒士想要的,对儿宽来说,眼下的生活,生不如死。
“儒家遭逢强权肆虐、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自祖师孔夫子起,奔波列国数百年,纵秦汉两朝,终究未遇文明之邦一展抱负,大汉气象,为师也看不懂,修文重武、百齐放。”
董仲舒始终想不明白上君为何宁愿费劲手段、心力重塑华夏思想,也不愿意让“整合”了华夏思想,甚至是更加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大放光明,“然则,大汉朝廷推崇强力,借重法家兵家,对我儒家多有打压,鲜能重任。
陛下虽说对我敬重有加,自即位起便多次崇儒尝试,但是,只以我门为驭民之用,今逢上君弃之如敝履,我门日后究竟能否作为大汉,乃至华夏根基,目下尚很难说。
究其竟,儒家是尚古复礼之学,是盛世安邦之学,是教化民众之学,是修身齐家之学,是克己正身之学,惟其如此,也是生不逢时之学。
时也势也,我儒家将有一段漫漫低谷,我门同人一定要强毅精神,受的起冷遇,要像墨家那般刻苦自励,方能复兴儒家于盛世之时。”
董仲舒只好把这一切都归结于陛下、上君是力求开拓的君主,将希望寄托于后世的守成之君,望着吾丘寿王,悲壮说道:“子赣须谨记圣人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弟子谨记!”
吾丘寿王被老师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整顿了心情,继续道:“对了,老师,至圣世家传来消息,已然举族西狩南阳……”
话没说完,董仲舒便上演了出医道奇迹,跳起打断,“你说什么?”
(本章完)